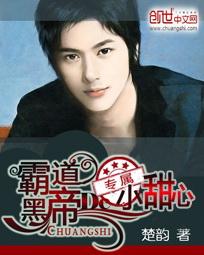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公子无疾无玉不医全文免费阅读 > 第185页(第1页)
第185页(第1页)
赢世安一笑,摇了摇头,“这只是我的猜测之言,这其中也是疑点颇多。你还是不要多想了,一切待裴云回来,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
可惜事与愿违,还没等到裴云回来,上京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北魏王毫无征兆地病倒了,摔了一跤,便不省人事,太医说是颅内大出血,能不能醒,何时醒,完全要看老天爷的意思。
要说这病,姜月是知道的,在现代叫脑溢血,要搁现代还有五成的治愈率,在这医疗匮乏的时代,患了这个病,基本上便是判了死刑。
然而,姜月自然是不能说这些,只入宫的次数变多了,一来她得侍疾,二来她得抽空宽慰宽慰王后。王后虽与王上不睦多年,却在听到王上病倒的那一刻,立时就软了下去,且一夜之间增添几许白发,成日里除了侍疾就是跪在小佛堂的团垫上,替崇微王念经祈福。
北魏王病了,忙碌的不只是姜月,不只是后宫的女人,朝堂之上,更是掀起了腥风血雨,两股势力各自为营,第一次泾渭分明地斗争起来。
太子一党皆言,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北魏王这个病况,立新君势在必行,按祖制,当由太子接位。
可赢机一党筹谋多年,又岂是好相与的?定然是反对赢世安登位,他们的理由倒也是冠冕堂皇:如今王上犹在,就立新王,岂不是明摆着咒王上早日归去。
一方欲立新王,一方竭力阻止,两方人马在勤政殿吵了三天三夜,仍是悬而未决。面上已是这般剑拔弩张,就更别提私底下的暗潮汹涌了。
这些日子,姜月感觉,这宫里的风似乎都染着血腥味,处处透着一种山雨欲来的飘零感。而风暴中心,注定是她的夫君赢世安,以及她姨母的儿子赢机。然而,赢世安自不必说,便是赢机,她也是不希望他有事的。姜月心中犯怵的事情,一天天逼近,姜月整日整夜地忧心着,连带整个人也清瘦了不少。她想劝赢世安,可是她也知道,这其中的关键不在于他,而在于那个人。
虽然有些不自量力,姜月还是决定做点什么。
这一日,姜月在王宫南门的城墙下,“偶遇”了两年不曾见过的赢机。他更黑了,也更瘦了。
两人沿着石梯,一前一后上到了城墙之上。北风呼呼地吹着,直刮得人脸疼,姜月捋了捋耳际飞扬的发丝,淡淡道:“表兄,好久不见。”
似是惊异于她的称呼,赢机转过头来望着她,唇角扯了扯,“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的表兄。”
“对不起,一直以来,都没和你好好相处。”
赢机失笑地说道:“我明白的,你连我娘的面都没见过,自然也不会对她的仇恨感同身受。而,你、你又跟了那人,便更不想同我有所牵扯,”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只是什么,她也说不出,转头,她叉开话头,“我这次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姨母的死,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可能是一个阴谋。”姜月将血书递给赢机,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赢机只稍微瞟了一眼,便将血书还了回来,漫不经心道:“你便是想要替那对母子开脱,也不必编造这样离奇的谎言。”
虽早已料到他这个反应,姜月还是苦口婆心劝道:“表兄,你信我一次,姨母留下这血书,定不是空穴来风,她和王上也定然是有仇怨的。我担心、我担心姨母将你当做了复仇的工具。”
“田希月,你没有资格批判我的母亲,你回吧。”
姜月还不死心,“表兄,我最后问你一句。如果姨母不是死于王后之手,你还是要同世安争个鱼死网破吗?”
赢机眼色一冷,转头盯着姜月,讥嘲道:“这才是你今日的目的吧?你要劝我放手?田希月,你未免对我太过不公!”
越描越黑,姜月都快急哭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我只是不想你们任何一个有事。”
赢机自姜月身上收回目光,合上眼眸,冷声道:“你走吧,你放心,不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你和孩子,毕竟,你们都是我母亲的亲人。”
姜月还欲再言,赢机摆了摆手,阻道:“不必再言。”
然而,赢机的确从未想过要动姜月,可别人未必这样认为。
是日,姜月循例去了王上跟前侍疾,王上的病还是老样子,除了偶尔动一动手指,眼珠子转一转以外,没有别的进展。
姜月自勤政殿出来,又去朝阳宫坐了一会,见天色渐晚,这才急急向宫门赶去。
这一日,月黑风高,姜月打着一盏灯笼,走在幽深死寂的巷子里,这巷子很深,似乎走不到尽头。许是太过安静,走着走着,姜月竟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