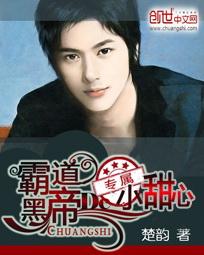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王爷为我造了反免费阅读 > 第28页(第2页)
第28页(第2页)
“是嘛,那借你吉言,”他似笑非笑,慢慢的将那一盏茶品完,才站直身子,随手将摆放在一旁的配剑拿上,别在腰间,对李日升道:“走吧,不为难你。”
李日升看了一眼那剑,只道:“王爷,进宫之人,不许佩剑。”
“谁说是要带到宫里去,我血债满身,要杀我的人那么多,路上防身而已,李公公不必紧张,进宫门之前,就交给公公保管。”
徐胥野换了件玄色外袍,轿撵和那匹名唤“破阵”的战马都在外面候着,昭成道:“眼瞅着天就要暗下来,王爷可要乘轿?”
徐胥野扣着外袍的扣子,修长手指灵活不停,“轿撵吧,让破阵歇歇。”
昭成了然,直到把徐胥野送出门才飞速跑回院中,敲响了西厢门,“任成哥,王爷被叫进宫了,王爷还说乘轿撵。”
他话说到这里,任成已经一转身,出了房门,纵身一跃,消失在屋檐之上。
王爷还未及弱冠之时,任成就跟了他,那时他刚刚统帅南护军,皇子年轻又是个不受宠的,清隽少年往那高山岭地一站,完全压不住场子,南护军那些头头谁都不服他,他手下亲信极少,处境艰难。
那时,还要与毗邻的契丹一族交涉疆土,越境去赴契丹那一场场“鸿门宴”时,就会问上这样一个“轿撵还是骑马”的问题。
若答“轿撵”,那便是要任成暗地尾随了。
他不骑战马情况有三,他自己受伤、战马受伤、或是故意让敌人知晓他放松了警惕。
天黑的早了些,徐胥野下轿撵的时候,宫里红灯笼已经透过一层薄纱散了淡淡红光。
李日升的心直到真的接过雍勤王腰间的佩剑才算是真正落了下来。
这位主儿,阴晴不定了,带剑进宫,不高兴了杀一个可怎么办。
甬道上宫女太监穿行,见到他皆战战兢兢行礼,有个小太监,见他多瞧了自己一眼,竟然还吓的尿了裤子。
不知道为什么,徐胥野突然想到那个小姑娘,她倒是不怕。
宫路黑且长,徐胥野问了一声,“本王这么可怕?”
李日升低头踱步跟着,“王爷那日在街头斩杀李副将,过于血腥了,消息传了过来,他们胆子都小。还有,王爷先前带着南护军杀契丹人的手段,过于阴毒了些。”
徐胥野脸不红心不跳,“你倒实诚。”
李日升道:“王爷自己也知道,奴才照实了说,那些个契丹人,虽夺咱疆土,但也是人,您断其手脚,碎其血骨,一家杀绝,连孩提都不放过,逼幼女为妓,实在是可怕。”
徐胥野乐了,慢条斯理道:“原来,我干了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