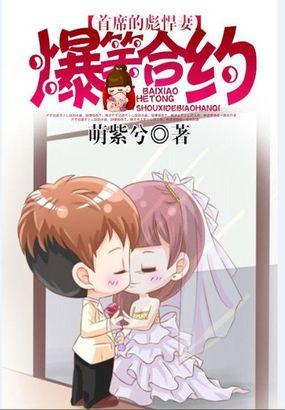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常人溺于所闻 > 第二十二章(第2页)
第二十二章(第2页)
冬云都还没说要做甚么呢,就被她打断了。冬云自然就听出来了,岑闻话里的别扭大过冷硬,于是她不易察觉地暗暗笑了,只说:那我叫厨房传膳过来姑娘先用吧。
听冬云说完,岑闻手上的动作更焦躁了,食指不安地蜷起又展开,脑中闪过前几晚疏雨递过来衣服时眼中的受伤。她倏然出声,闷声问道:有人去给她送餐食吗?
没有,老夫人身边的婆子一早就把雁乔使唤去前院做活,估摸着,就是不想让她去送饭。
看着岑闻神色,冬云补上一句:眼下,大夫人已是一天未进食了。
岑闻抬了头看向窗外,暮色渐沉,云外余晖似裂绯,烧得她心慌意急,她有些坐不住了,便僵着个脸转头嘱咐冬云:你拿个软垫,叫厨房做一份我的餐食,清淡点,拿食盒装了,再
再拿一碗水,同我过去。
冬云心中暗笑,嘴上恭敬回道:哎,好
疏雨跪了半日,腿早已没了知觉,她一把跪在蒲团上时,听婆子传话说老夫人心慈,念在她平日贞顺,只让她跪到子时,长长记性就行。
她听了心里更是好笑,一时不知先笑婆母心慈,还是先笑自己贞顺。她也懒得再争甚么,一言不发地就这么跪了,一跪就是三个多时辰。
此时外头余晖已尽,有女使来掌灯,祠堂灯火通明,那亮光晃得她眼睛轻眯。
早间,她只吃了粥饭,现下胃里已是饿得绞了起来,没有听到雁乔来过的动静,估摸着是被前院下了令扣下了,想到此处,她叹了一口气。
正想敲敲那酸麻的腿,便听到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雁乔走路向来散漫,来人脚步声规律,一声声叩在疏雨心上,她便有了几分猜测。心跳快了起来,咚咚敲在胸间,震得比庆云寺钟鸣还要响。
那人靠近了,推了门,从暮色里踏了进来,碧色衫子,小山眉,眼中揉皱了两波秋水。
她轻轻走来疏雨身边,没有低头,漠然地看了眼祖宗牌位,然后将那食盒放在疏雨手边,又把软垫放下,静静问道:你向来最懂规矩,怎么会来罚跪祠堂?
疏雨看着食盒,心中暖意流动,可她哪能将始末告诉闻儿,便搪塞道:自然是我失了言,惹了婆母心烦。
你能失甚么言?你这张利口,从前不是擅言辞。
嗯,这不就是最不守规矩的地方么。疏雨听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起来,她以手扶着地,颤着笑了起来,这笑声几分讽刺,几分自苦,听在岑闻耳里不是滋味。
岑闻于是转头过来看着她,看她笑歪了去,但双腿纹丝不动,梗声问她:膝盖不疼吗?
疏雨听了她这句,笑声停了下来,眼中带了几分柔软,我撑得住。
疏雨看着岑闻,岑闻也在看着她,对上眼神的一刹那,她捕捉到了岑闻眼中没来得及藏好的心疼,疏雨舔了舔嘴唇,心中有酸涩漫上来。她怕被闻儿这般看着,她承不住。
于是疏雨压下鼻间酸意,柔声对岑闻说:你能不能替我去跟雁乔说一声,她定是被前院婆子为难了,叫她别担心我,顾好自己就行。
岑闻听了这话,那还没来得及压下的心疼化成了薄怒,她冷笑一声,你自己尚且顾不住自己,还有心管雁乔吗?
疏雨四两拨千斤,只顾柔柔望着她,淡淡地回她:所以这就得指着你了。
岑闻被她拿这话一堵,气也没地出,她闷声道:你倒是心里清楚。
李氏不是第一次罚你跪祠堂了罢。
那自然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从前的由头是侍奉不利,今日的由头是顶撞婆母。疏雨轻飘飘将话茬揭过去,记不清了,横竖再跪两个时辰就能起了。
想了想,又嘱咐道:你一会儿就走罢,别又落了那些下仆婆子的口舌。
岑闻听了,也知道留久了,那些下人又要去告那作恶老妇,于是转身要走。她嗤笑一声,边走边撂下一句:随他们怎么说。
疏雨回头凝着她,心里想着,她确实一直是这般恣意自在,大抵遇到了我,才给她自己讨来了不自在。
她眼看着岑闻就要推门出去了,摸到了手边食盒,想借力转过身去,她轻喊了一声。
闻儿。
翻过这几日,就是中秋了。
带着几分希冀,她斟酌说道:今年中秋灯会,再同我一起出去吧。
岑闻身子顿在了门口,半晌不出气,当疏雨以为等不到回音了的时候,她才回了一句,声音僵硬的你先当心你的腿罢。
到底也没直接拒了她,疏雨笑了出来,垫上了软垫,膝盖上舒服些了,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食盒,里头呈着饭菜,有盐醋肉脯,有白蒸鸡,还有一盅清炖冬瓜。最底层放着一碗清水,岑闻倒是细心,知道她饿了一天,唇焦舌燥,需用得清淡些,疏雨摸着食盒,心里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