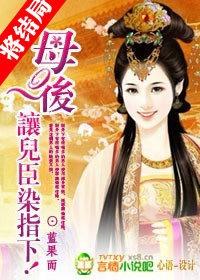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辛弃疾青山不负我 > 8 第 8 章(第2页)
8 第 8 章(第2页)
“嗯。”
容萸端着蜜水进了屋,他正半倚半靠坐在床上。他虽满身的伤,可只要他醒着,不管她何时进来都能看他穿戴整齐地坐着。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即便身处茅屋,仍旧难掩浑身的清贵气度,就连乡野间最常见的粗陶碗在他的指间也变得贵重起来。
“你再想喝就叫我。”容萸接过他手中的空碗,轻声说。
闻人翎还未回答,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隐约听到女人的哭声,在喊容萸的名字。
“我出去看看。”容萸给他掖好被子,走了出去。
院子里来了十多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头上包着头巾,身姿丰腴的妇人。
她看到容萸便冲了过来,叫嚷着:“容萸,我相公是不是在你这里?”
来看热闹的人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院子里顿时吵吵嚷嚷,像出了笼的鸡鸭叽叽喳喳闹不停。
容萸有些发愣,不知道这妇人的相公是谁,为何找她要人?
“王氏怎么找容萸要人?”
“陈锁跟容萸有一腿——”
“啊!容萸阿娘之前就不检点,没想到生个女儿也这样!”
人群里炸开了锅。
王氏的目光从容萸呆愣的脸上,滑到她该鼓鼓该细细的身体上,叉腰骂道:“有人看到你在村口勾搭我相公陈锁!他这几天不见了,是不是你给他藏起来了?”
听到陈锁两个字,容萸浑身的血液顿时冲向脑门,脸色倏地变了变。
“我、我没有——”容萸脸色苍白,着急忙慌解释。
“不是?三月初七晚上有人看到他往岭头这边走了,这里只住了你一家人,不是来你这里还能去哪里了?”
容萸紧张地扣着手,指甲断了也浑然不觉:“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
指缝里冒出点点鲜血,她浑身冷得像站在冰窟里。
王氏尖着嗓子喊:“你不知道?村里的人都看到过好几次了,你还想抵赖!你要不要脸,小小年纪就勾搭别人的相公!下贱!”
春雨淅淅沥沥,村子里的人没法下地干农活,听到这边的动静,纷纷走了过来。
“陈锁,你给我滚出来!”王氏和她娘家人料定陈锁跟容萸有所勾搭,推开容萸气势汹汹往屋里闯去。
王氏是出了名的泼辣,没人敢拦她,任由她从正屋冲进去翻箱倒柜。
她泄愤似的,把屋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晾在堂屋的草药全被扔到地上,被人踩来踩去。
“容萸,你要是知道陈锁在哪里就告诉她吧?”有人上前扯了扯容萸的袖子,劝道。
容萸一把抽回袖子,吸了吸鼻子:“我不知道告诉她什么?”
“三月初七晚上,李老赖亲眼看到他往你家来了。从那天起他就不见了,不是你把他藏了,他会去哪里?”
容萸眼圈绯红,浑身止不住颤抖。
“瞎嚼什么蛆。”伴随着中气十足的一声骂,一杆阳叉杵到了那人的腰上。
她“哎哟”一声,捂着腰转过身,看到杨婶拿着杆阳叉怒气十足地站在她身后:“杨三家的,你干啥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嘴里嚼蛆的东西。”杨婶一把将容萸护在身后,指着那人骂,“陈锁是啥香饽饽吗?也值得我们阿萸惦记?他那种烂货,给咱们阿萸提鞋都不配,少往他脸上贴金了。往岭头走就是来找阿萸吗?那死鬼喜欢喝酒,万一是他喝多了马尿,要去跳河呢?”
屋里王氏翻箱倒柜的动静极大,转眼间他们从正屋搜去了边屋。
王氏推开边屋的门,微弱日光照出床上的轮廓身影。她以为是陈锁,骂了句:“死鬼,可让我好找!”
冲上前揪他起来。
“放手。”闻人翎声音清冷,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