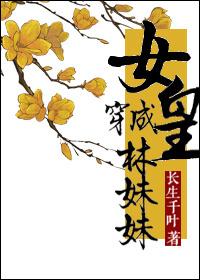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庭有武陵色微雨琼昙 > 第24页(第1页)
第24页(第1页)
“嘿嘿,得令!”苏云澈翻身上马,雾霭朦胧中一骑绝尘。何莲扶着肚子,静静地望着苏云澈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那心心念念的身影,任由一身红衣似火在风中摇曳。不远处的皇城内,夏知瀚的寝宫灯火通明,映窗亮了一夜。金樽烈酒入喉,却更煎人寿,再难以浇愁,夏知瀚醉里挑灯,抚摸着壁上悬挂的那张巨幅形势图,梦回当年午夜风雪吹角,千帐灯火连营。当年激昂,豪情雄壮,转念想来,这哪是一幅区区薄纸,这是年少时他和君翎携手,一点点收复起来的江山。就算当今局势风云潇潇明暗,夜雨狂澜,身为大夏君主,他怎能容忍那北疆狂风凄寒,饿虎豺狼来犯。脑海中回荡君翎启程前向他许下的誓言。“卿卿坐明堂,末将赴边疆。凫雁不渡塘,燕然勒回乡。”天子镇八方,风仪慑胡狼。山雨欲来催楼殇,危急又何妨,忠骨铮铮舍了一时儿女情长,便成了这盛世大夏坚硬的脊梁。萧灼华渐渐习惯了独居于城郊小院的清净日子。他变得越来越嗜睡。阴雨天身上的旧蛊难免作祟,带起多年的心疾,萧灼华点了暖炉,裹着厚厚的棉被,像猫儿一样迷迷糊糊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听着窗外雨打霜叶发出闷响,檐下的银制风铃叮当,忍着百爪挠心一样的疼,冒一身冷汗,一天都不想动弹。头疼发热也断断续续折磨着萧灼华,他就算虚弱得快要走不动路,还要强撑着给自己煮一碗汤药服下,忍住强烈的呕意,拥着被子倒头便睡,睡醒了仍是觉得天旋地转,引得他又气短,从早到晚粗喘咳嗽着直到病的劲头过去,已是夜雨五更寒。他变得喜欢晒太阳。天气放晴时,萧灼华把摇椅从屋子里搬到回廊下,肚子到脚面都覆盖着暖融融的锦被,眯缝着眼看树杈间的光,遥望着四方院墙里的云彩缓缓游荡。他的人间静得像一池闲塘,仿佛能听见时间在与世隔绝的小院里流淌,任由白日的艳阳换上红纱的霓裳,不觉间搅动了漫天暮色苍茫。每天喝三四碗苦涩的药汁调养着,萧灼华的胃口也比先前好了不少,能勉强吃下些清淡的饭食,原先脸上的苍白气色红润了不少,衬得他本就好看的五官更加清丽夺目,肚子不知不觉就鼓起一个小小的弧度来,尽管没什么必要,但他很早就将自己衣服的腰口改宽一点,生怕憋屈到了孩子。从他的孤宅再往南走,是一处农家的集市,他没力气便罢,有力气走路的时候一定会去买些老农的干菜、新鲜的鸡鸭鱼肉囤起来,变着法想给小桃子补补。处理荤腥的时候气味重,他一边干呕到流泪,一边收拾案板上身残志坚想要和他抗争到底的鲫鱼,时不时和肚子里的小家伙轻语:“你乖一些,别让爹爹吐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卖鱼的大娘说吃了对孩子好……呕……”集市摊子上的心善的村妇多半都和他相熟了,知道他犯病时来不了,常常给专门留着些好菜等他来了再买。她们打趣萧灼华生得出奇美貌,村子后山庙里的娘娘下凡怕是都不及他半分。萧灼华红了脸,被夸得不好意思又不怎么会接话,只好腼腆地笑。“总是见公子独自来买菜,你都有了身子,怎么不见夫君陪着?”这天在集市,小菜摊子前慈眉善目的老妇人问他。“我的夫君啊……”萧灼华眼底泛红,掩不住心上的忧伤,低头看着菜篮子的竹编把手,呆滞了一刹那,随即又回过神来,抬头吸吸鼻子,强颜欢笑着回答,“我的夫君在北疆打仗呢,我………我等他回来……”“哎呀公子莫要愁,我家老头子也被征去了。你大可放宽心,当今北疆的三军大统领,咱们堂堂定北侯大人何时打过败仗呢。再说了,顾将军那是出了名的爱惜将士、英明神武,将士跟了他打仗准没错,咱们夏家的士兵此次定能大捷而归。”老妇人急忙安慰他。萧灼华听得愣了神。小时候在他怀里撒泼打滚的奶团子,如今已经这么厉害了吗。他心底泛起一丝丝骄傲,哼哼,我的夫君就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不对,他被休了,顾煜早就算不得他的夫君了。哼哼,我孩子的父亲是天下最厉害的。萧灼华依然骄傲。萧灼华笑容满面地跟老妇人道了别,像只刚觅食完的小松鼠,抱着一堆菜蔬鲜肉美滋滋地就要回窝。走着走着,他看到街边的墙上有一幅他的画像。像是挺像,但怎么画得这么丑。萧灼华皱眉。唉不对,这不是重点啊喂!萧灼华纳闷地走上前,看清画像下方写的一行字。前朝罪奴,萧氏余孽,活捉者押至天衣署,赏黄金二百两。萧灼华瞳孔一缩,顷刻间已是满身冷汗,怀里堆成小山的东西随着他的颤抖掉了一地,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了。他扑上前挡住墙上的画像,用双手慌忙地把画像狠狠撕下,揉成团摔在地上。他剧烈地喘着气,感到背后一阵发凉。犹豫着回头,他看见身后的街边早已贴满了和刚才那张一模一样的画像。路人贪婪的眼里露出饿狼般的凶光,一个个直勾勾盯着他。“抓住他!”萧灼华意识到事情不对,拔腿就跑。“往哪跑!”刚刚短暂为画像停留的人们如夜潮般冲他汹汹而来,快要将他吞没,一个高大粗野的屠夫跑得最快,咯咯阴笑着,脸上横肉狰狞发红,扛着明晃晃的刀,泥手抓住萧灼华雪白的衣摆,向他的背上砍去。“啊!”萧灼华侧身一躲,奈何身手早已不及当年敏捷。虽然让这一刀避开了背,但尖锐的刀刃还是重重划开了他的右臂,甩出一大片暗红的血来,泼了萧灼华一身,宛如在白衣上炸开了诡异的烟花。萧灼华死命挣扎,衣摆“刺啦”一声撕裂到大腿根,露出单薄的里衣,凉风飕飕吹过来,他也顾不得冷,左手摁住血流不止的右臂,跌跌撞撞像只受惊的野兔一样窜进七扭八拐的巷子。“要看脚下……不能摔……”萧灼华一边逃一边哆哆嗦嗦地提醒自己。他怀着孩子,平常就算劳累了都会腹痛难忍,如今一旦不慎摔了跤恐怕就再也爬不起来,只能任人宰割。“该死的畜牲!”萧灼华听见有人咒骂他。狭窄的巷子不容太多人通过,趁着人潮被巷子口挤得停住,萧灼华没命地奋力跑着,故意绕了一个假弯,避开搜寻的人再回到原地,拐进了巷子里最深最窄的一条羊肠小道。萧灼华把衣袂撕下来一大块,叠起来按着伤口,生怕留下血迹暴露了行踪,眼看着血浸透了布料,他体力也越来越不支,腹部也下坠着疼,他担心孩子受不住,吓得心慌,不敢再跑,只好拐进身旁只容一人通过的废弃死胡同,尽头堆满了倒闭的裁缝铺子留下的废布料,他侧着身子一溜烟钻进去,靠坐在尽头,拉起地上一块很大的破黑布盖住自己。“你看他的肚子,一看就是有身子的人,一个孕夫跑不了多远的。”“就是,不要脸的东西,一个孽障比鱼都滑头,难抓死了。”“分头找!到时候黄金平分!”萧灼华在破布上撕开一个不明显的洞,留着用来呼吸,刚才跑得太快,他坐在地上痛苦地缓了好久才喘上来一口气。布满灰尘的破布闷得他的肺又痒又疼,他憋得快要窒息也不敢咳嗽。萧灼华找一块厚实的布盖在伤口原先的白布上,看着已经渗透出旧布的血又渲染了新盖的布。刚才受伤的时候,萧灼华一心要逃,害怕得身上都麻木了,没想到现在会这么疼。肚子里的小家伙大概受了惊吓,钝痛渐渐从小腹蔓延到五脏六腑。萧灼华就算左手紧紧摁住伤口也抵不住划得太深,血一时还止不住。右臂疼得快没知觉了,也抬不起手护住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