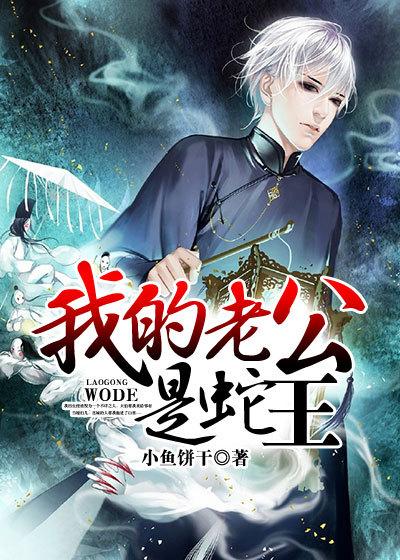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柏梁台象征寓意 > 第226章(第1页)
第226章(第1页)
怪老头的每一句话都刻在她心里,他幼年不易,他背负太多,他行事自有原则……她不能怪他,也无法怪他,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是她父皇。她想挽救这种局面,想助他放下仇怨,多担待些多忍受些,也在常理中。
可越坚持越心灰意冷,他的心如冷得如三尺厚的冰,他的原则如城墙铁壁般坚固,仿佛她做再多事都只是徒劳。即便是这样渺茫的希望,她仍然没有放弃,可如今他马上要去东瓯国,她的坚持还有意义吗?
她一步步走向他,轻轻地抓住他的手臂,仿佛濒临死地的鲤鱼在做最后的挣扎,声音中带点嘶哑与希冀:&ldo;你,可以不走吗?&rdo;
那只手臂轻轻扯开了,她的手上蓦然一空,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她以为她会勃然大怒,会歇斯底里,但奇异的是,她的心境格外平静,像那无风无浪的水面,平静得连波动的涟漪都没有。
也许自始至终都是她在自欺欺人,那堵信念之墙早已坍塌,她终将为自己的坚持划上终点。想起那个费心雕刻的玉佩,她从腰带中取了出来,目光静静抚过那只兔子:&ldo;也许我真的没有送你礼物的命……&rdo;
她忽然握紧那个玉佩,狠狠向地上一砸,那块玉佩摔在石上,碎裂成片,如她支离破碎的心,但她说出口的话却异常坚定:&ldo;江玄之,我放手了,以后再也不会纠缠你了。&rdo;
第97章第97章逝者之心
寻梦在章台路遇上了怜心,那丫头一脸急切地过来找她,说是夫人病重,让她赶紧回宫。寻梦心头一慌,却转身折回安置所,拉上崔妙晗一同赶回宫。
寻樱的心疾本就严重,前几日被萧青拍了一掌,心口疼得无以复加,但她不想耽误了寻梦的事,严严实实地瞒住了她。直到今日,她感觉自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心里藏着许多未尽之言,怕不说便再没有机会,这才让怜心去找寻梦回来。
寻梦回到凝香殿时,殿内的油灯刚刚燃起,不知谁的影子斜斜印在窗纱上,一边漆黑一边暖黄,如阴阳相交,生死相隔,让她原本七上八下的心境越发凌乱不堪。
她甩下脚上的鞋,一头冲进殿内,殿内充斥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几个侍女躬身站在一旁,父皇坐在床榻边,似乎在与阿母说话,而阿母那张脸被油灯照得蜡黄肌瘦,唯有那双眼依然明亮,神采飞扬。
刘贤易缓缓从床榻边起身:&ldo;与你母亲好好说说话吧。&rdo;
他的眉间隐有疲惫,这几日他被一堆破事搞得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局势,让众诸侯安安分分地离开长安。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看樱娘这情形,怕也就剩这一两天了。他远远地避到窗前,凝望着幽暗的窗外,那萧瑟的冬景仿佛荒凉到了他心里。
寻梦还没靠近床榻,猛然想起临时被她拖来的崔妙晗,要唤她进来替阿母诊治。寻樱心知自己药石无灵,出言拒绝,但拗不过寻梦坚持,终让她将人唤了进来。
因陛下在殿内,崔妙晗没敢直接闯进去,听到里面的叫唤声,才举止落落地走进殿中。路过刘贤易身边时,她微微施礼,在他略带探究的眼神下,不紧不慢地向床榻走去。
崔妙晗曾替寻樱调理过心疾之症,对她的病症了然于胸,可今日搭上她的脉,脸色骤然一变,脉象怎么如此微弱?之前她的心疾之症明明稳定了,为何陡然生出这样的变故?
&ldo;妙晗,怎么样?&rdo;寻梦看她脸色不好,焦急地问个结果。
崔妙晗抿了抿唇,歉疚地冲她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寻梦眼中那希望的火光瞬间一熄,身子微微向后一泄,仿佛失去了大半气力。当初妙晗说可以用针灸和药物替阿母调理,保她两年无虞,那时她便知道不可能有两年,因为阿母的情绪不可能毫无波动。她早有心理准备,与阿母相处的时间也许只有一年,甚至是几个月,但她万万没想到竟然短得只剩几天。
寻梦脸上浮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寻樱见了心知不妙。她性情外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可此刻她竟如此平静,如此反常,莫非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思索片刻,寻樱温和道:&ldo;陛下,你们出去吧,我有话与梦儿说。&rdo;
刘贤易默默环顾殿内,沉声命令道:&ldo;你们都退下。&rdo;
众侍女应声而出,刘贤易也跟着向外走,忽然又转身瞧着寻樱,道:&ldo;朕就在外殿,你若有事,可叫唤一声。&rdo;言罢,快步走了出去。
等到殿内只剩下母女俩,寻樱伸手握住寻梦的手,惊觉那只手冷得像冰,往手心拢了拢:&ldo;梦儿,你是不是冷?&rdo;
寻梦常年手脚冰凉,早已习以为常,直到阿母手心的温度传来,她终于感觉到自己的手是冷的。她瞥向旁边的火炉,炉中炭火烧得所剩无几,连忙站了起来:&ldo;我让人添点炭。&rdo;
不料寻樱拉住了她:&ldo;上来赔阿母说会话。&rdo;
话落,她向内挪了挪虚软的身子,腾出一片空榻,寻梦顿了顿,依言钻进了阿母的被褥里,满被子的暖意席卷而来,似乎真的不那么冷了。
寻樱仍是捂住她的双手,余光瞧着她沉静的面容,迟疑道:&ldo;梦儿,江玄之仍然无法接受你?&rdo;
寻樱明显察觉她浑身一僵,如血液凝固了一瞬,但她很快松了下来:&ldo;他过两日便会去东瓯国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