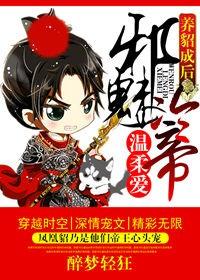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蝴蝶骨一枝枯芙高干 > 第五十六章朱丽叶需要救援吗下(第2页)
第五十六章朱丽叶需要救援吗下(第2页)
“她19岁,还在读书,是冯毓伊的侄nv冯露薇。”
话音刚落,一耳光意料之中落在他脸上。
“你疯了吗?”父亲怒骂他,“19岁?你生怕不被人拉下泥潭?”
贺青砚左脸发麻,微微闭了眼,张嘴竟有些吃力,“我会承担我的后果。”
母亲愕然到这时才缓缓出声:“青砚,你怎么会和那么小的nv孩……”
“你想都别想,我不会同意!”父亲的怒意几乎要掀翻书桌。
“据我所知,我个人的婚姻状况,不需要经过您审批。”贺青砚笔挺站着,他的眼神坚不可摧。
父亲却静下来,怜悯地看着他,看一个为情所困的疯子,“你已经失去理智了,贺青砚。我能让你待在现在的位置,也能让你掉下来。”
“您不会,我现在还很有用。”贺青砚笃定地笑了笑。
“我不和疯子说话。”父亲折身往外走,声音冷漠地飘进来,“去北边祠堂跪着,冷静了再来和我谈。”
贺青砚回头,母亲正看着他yu言又止。此处太暗,母亲的脸坠入墨se,他辨不清那是慈悲还是恐慌。
“您也要斥责吗?”贺青砚无所谓,脸上挂着笑。
“我只有一个问题。”母亲审视他,冷静而严肃,“你和她之间的关系,是由你b迫才开始的吗?”
“不是。”
他听见母亲松了口气。
生活助理像道幽灵悄然而至,挡在进光的正门口,“贺书记让我带您去祠堂。”
母亲拍了拍他的肩膀,大概是宽慰。贺青砚有得选,时至今日没人能拦住他的脚步,但如果罚跪是谈判的交换条件,他乐意领受这种侮辱。
他在一鼎香炉前跪下,四处无人的厅堂,没有人告诉他需要跪多久。白烟熏过他的脸,他穿着皮鞋和西k,大腿布料绷直,k脚荡在地面,灰尘正悄悄爬满他。
双膝跪地,年幼时都未曾有过的惩罚,成年后更天方夜谭,此刻他直直跪着,这对他而言不代表服从,反而是叛逆的铁证。
付出代价后,就不必再为忤逆感到愧疚。
起先是酸胀,后来身t麻木不觉,他维持笔直的身姿,看自己影子随太yan朝东转,逐渐暗淡成透明,月亮从身后升起来了。
母亲忽然闯进来,拿着他的手机焦急喊他,“青砚,冯毓伊的电话,好像有急事。”
烛台火苗一颤,贺青砚想站起来,双腿充血猛地摔倒在地,缓了几秒才拿起电话。
“怎么了?”贺青砚眼前白茫茫一片,麻木的身子正迟钝恢复血ye循环。
“小薇不见了,坐着她男友的车不知道去哪里,手机也关机了!”冯毓伊声音急躁,像几百根针扎过来。
贺青砚愣了一瞬,血ye从心脏倒流,“不见了?”
他撑着手臂,竭力站起来,掌心擦破一块血红,焦急地朝外走。
木门开了两扇,夜晚的穿堂风从他耳侧呼啸,灭了两根烛火。
电话里正匆忙交代前因后果。冯炳给冯露薇安排相亲,也是第一个发现冯露薇跑了的人,监控只能追到山庄大门口,两个年轻人的背影钻入省道,就跃出他的视线范围了。
贺青砚挂断电话,呼x1急促,强行让自己缓冲两秒,才拨通颐市公安局的电话。
“是我,全市道路出口设卡,查一辆摩托和两个人。”
他顿了顿,“扣下以后,把人分开拷上,等我去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