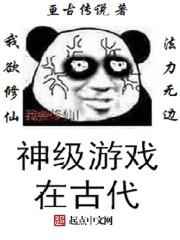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火不灭上一句 > 贰拾肆 呕哑(第2页)
贰拾肆 呕哑(第2页)
她本来就没多坚定,干脆顺势倒了回来,砸得陈禁戚闷闷地痛呼一声,应传安笑了,道:“殿下是打算今晚睡在这里?”
陈禁戚不说话,就从背后搂着她,搂得死紧,应传安能感受到肩颈边时有时无的气息,还有身后紧贴的全然放松的柔软身躯,她不自在地绷紧了脊背,让两人间留出些体面的间隙,他舒舒服服躺着,她却僵硬无比,完全不敢再去贴上。
“……”坐了片刻,应传安突然僵硬地直起身,连坐在此处都不能再忍受,催促他,“殿下,放开我…”
陈禁戚没应声,应传安是真急了,“殿下,我没开玩笑,别…我该就寝了…嘶……”
得寸进尺的,陈禁戚凑到了她耳侧。应传安额上沁出了些冷汗,只觉得脸上热得快要融化,她把双腿叠起来,真心实意地想把反应压下去,但愈是在意,她的感知就越灵敏,腰边他跪坐的腿,眼下圈住她腰肢的手…玉一般的手腕,蜷起的手指,还有此时近在咫尺,浅色,细腻的牡丹花瓣似的唇。事态似乎要重蹈覆辙。
“知县这就睡了?不再做点什么吗。”陈禁戚说。
“……操。”应传安忍不了了,随便从手边扯下一件衣裳,反身蒙住他的脸就带着他躺倒,她转过去骑在他腰上,手上暗暗使劲,像要把他闷死一样,“殿下,我再说一次,我真的…”不想。
应传安噎住了,怎么也说不出后两个字。她难道真的不想吗。她其实就是恼羞成怒了,她想,太想了,就是因为太想了才一刻都不想和他多待。她的先前谋划中从来没有他,凭什么突如其来地牵引她的魂梦,凭什么无缘无故占据她所有心绪……凭什么要把心割出去一半,割给一个位高权重,轻易就能决定她生死的人。何况如今世道衰败,太平犹危,阵营殊立,届时又该如何相安。
她难受好久了,简直受够了,真的受够了,又有谁能欣然被情欲所控。然而,然而。应传安手下越来越重,织金的衣裳,碧色连枝纹样,针绣的舒展花叶逐渐出现了重影,她呼吸愈渐急促,陈禁戚竟然无动于衷,静静地躺在她身下,只是胸膛起伏不定。任她动作。但难道真的如他表面一样乖巧?他难道从始至终看不出她的焦虑和挣扎,他难道不清楚二人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沟壑?偏偏还要屡次三番来撩拨,偏偏装作一无所知,偏偏肆意妄为,怎可能是真的不清楚她……都是他的错!
最后偏激地给他定了罪,应传安为自己的念头所惊,她何时竟然如此娇纵,心安理得地地把过错全然推出去。她张口喘气,血腥味在唇齿间弥漫,她才意识到原来一直咬着自个儿的唇瓣,仿佛如梦初醒。她匆匆松了手,陈禁戚一把扯下衣裳,侧过脸,剧烈地咳嗽起来,面上湿漉漉,真是被折腾狠了。
“……”
“……”
应传安捂住脸,闷声道:“殿下……”
欲言又止。她其实并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不太愿意去看他作何反应。耳边是一阵阵沉重喘息,身下的躯体抖得厉害,看来是真的不适,窒息得难以忍受。但她难道比他轻松半分。
事已至此,先走再说。应传安起身就要溜,还没出柜门脑袋就狠狠在框上磕了一下,咚的一声,她捂住额头坐了回来。
逃脱未遂,应传安尴尬万分,低头一个劲儿揉脑门。
“……”
陈禁戚没好气道:“得亏没听到水声呢。”
应传安想犟嘴,斟酌片刻,还是道,“殿下到底想做什么,我还有公务在身,真的该就寝了。”
“你倒是去。”陈禁戚戳了戳她的大腿,抬眼给了她个正眼,“走一半又倒回来的人是谁?”
应传安默默护着头爬出了柜子,她站在柜门前,低头看着窝在柜子里的陈禁戚,忽然理解了金屋藏娇是作何心态,她半关上柜门,从缝隙间探头对他半假半真道:“殿下还不出来就睡里边吧。”
对峙片刻,陈禁戚抬手,微微扬起下巴,好像在示意什么,应传安叹了口气,搭手上去牵他起来,他起身后一点力气都不使,直接往她怀里栽,带得应传安一个踉跄差点又摔了,陈禁戚反倒贴着她笑了起来。种种反应,让应传安怀疑他是不是喝了假酒,怎么一会儿赛一会儿不正常。
“那就祝应知县好梦了。”陈禁戚嘴上这么说,眼神饶有深意地往她身下瞥。
应传安迅速明了他发笑的缘由,现在也不羞恼了,反是从之如流:“殿下不必担心这个,实不相瞒,说来殿下是夜夜到我梦中帮我疏解,想必今晚亦然,实在有劳。”
确实把陈禁戚恶俗到了,她言之凿凿,目光坦率,神色自若,楚楚杏花眼,湿飞芙蓉面,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人淫词浪语是张口就来,手黑心又狠。当真是衣冠君子,两面禽兽。
二人相望,最后罢了,陈禁戚拂袖离去,应传安长吁一口气,倒在床上轻轻喘气。
连轴转了两三天,铁打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明日将有更大的风波,这么大的烂摊子,她实在有些孤立无援。
郧阳内部更是混乱,连盐铁酒税都不归官家涉手,而握在各大宗族手里。有关重权高利,她竟然在当看客,而各类繁杂小事的简卷倒全落她手上,好像一众官吏都是吃干饭的。
从下到上都各怀鬼胎,各有根系,难怪上任知县只是一个劲儿给自个谋利,原来是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不如当个傀儡吃些漂没,起码不用担心被暗杀。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不得而知,郧阳割据称王?天下分裂?大祸积于须臾,也不知现在干涉能否掐住势头。
夜过将半,应传安惊醒了一次,半梦半醒,听到窗外雨声嘈杂,恍惚地下床,卷帘看了会夜色,窗外春花打落,一地惨白,雨水汇聚成流,她又放帘,魂似的飘回床上再度睡去。
**
“应知县!”
裴関加紧打马,终于追上了前头就快隐没在雨里的一人一马。
那白衣娘子忙着转过头来看她一眼,被雨水浸透的面上端是心神不宁,她形容狼狈,未梳成的发髻此时快散完,及腰的墨发和清浅的素衣随水沾在身躯上,全无半点风范可言。然而她心思不在这上头,一个劲打马直前,雨水倒涨,淹过马蹄,她不出一柱香,居然硬是过了十数里地。裴関只不过比她晚一脚出门,都要追不上,现在才捉到人影。
不过看清来人后,应传安倒是稍微勒了马缰,与她并行。
一夜过去,大雨半点要停的迹象都没有,反到淤积泛滥。应传安克制住心头烦忧,强打精神,对她道:“听说蜀中多雨,若逢上几日不霁,骑马上路似乘船过江。今日才算见识到了。”
“划船可不能照知县这个速度。”裴関抹了把脸上的水,“已经这幅局面,急切也无用。知县还是多多当心路况。”
应传安摇头,再去看眼前,雨帘后白茫茫一片,都快看不清路,只能凭记忆行驰。她喃喃道:“我只是…心如悬旌,不能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