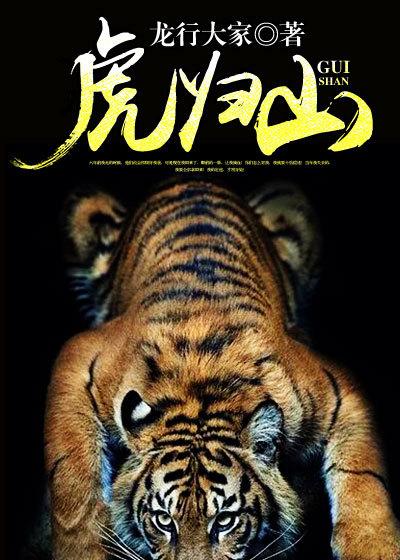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卿何如我? > 第27页(第1页)
第27页(第1页)
她手下也有五六处铺子,不过多是些脂粉、衣料、笔墨一类的小生意,账本虽看,但也不曾如何上心。
哥哥一下子把陈家在京城的全部家业都交给她,然而她从未在这方面下过功夫,跟着陈家资格最老的吴掌柜学了些时日,但此刻面对着林林总总的账目,仍感无处下手。
况且哥哥还让她做出一番气候,她想着朝廷每年拨给漠北的军费,长叹一声。
捡枝打了帘子进来,附耳说道:“姑娘,郑公子来了。”
哥哥把京城一大摊子丢给了她,自己跑去了浙江。临行前倒也没有真的撒手不管,替她寻了一个人来,说对她的“一番气候”有大用。
陈寻雁如何也不会想到,哥哥替她寻来的人是通政司右参议郑永佩家的二少爷——郑又戈。
郑又戈与她同岁,瞧着却比她还瘦弱些,心中念着,京城传言郑家继夫人对先夫人遗下的郑又戈极差,似乎所言不虚。
郑又戈面色苍白,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袍,行礼时,陈寻雁瞧见他的脊骨瘦得凸起。
前两日,他触怒了王氏,王氏到父亲面前一番哭诉,他又被罚跪祠堂了。
正当他跪得又累又渴,第十三次发誓定要叫王氏付出代价时,一个黑衣人把他从祠堂里拎了出来,送到了陈霁面前。
艳冠京城的大公子,端着茶杯悠悠品了半晌茶,才道:“郑又戈,你想替你娘报仇吗?”
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面前郑又戈眼中野狼一样的恨意,与他梦中日后那位呼风唤雨的商业巨贾重合起来。
陈霁用碗盖虚虚撇了撇不存在的茶沫,自己提前把郑又戈从苦海里捞出来,换他给自己卖几年命,这笔买卖,实在划算。
陈寻雁道:“郑公子,请你来的意思,想必大公子已经解释清楚,我不必多言。但是在合作开始之前,请先让我看到你的能力。”
郑又戈毫不客气地坐下,“陈公子只管问,生意上的事,我定知无不言。”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必须抓住。
陈寻雁为了在外行走方便,着了男装,不过并未多加修饰,细细瞧着也能瞧出来。
“这里是一部分铺子地契,郑公子拿去瞧瞧,何处有不妥、需要改进的地方,给我拟出个条款来,一日期限。”陈寻雁将黄花梨木匣大大方方地推给郑又戈。
郑又戈也不赘言,直接开了匣子将全部地契拿了出来。“不需一日功夫,一炷香便可。”
郑又戈指尖捻着几张地契,看了几眼便道:“公子手下有五家脂粉铺子。南烟斋卖的江南蜜粉,水光阁也有。泛彩居的镇店之宝海棠口脂,流烟台中也寻得到。何不统一旗号,既壮大声势,做到提起脂粉铺子便是公子的商号,又免得自家铺子打混战呢?”
“再者,女客用了店中的脂粉,若脸上生了疹子如何处理?若客人用过了又觉得不合心意,可以退货吗?这些问题公子可有安排对策?”
陈寻雁思索着,点点头表示赞同。
赵又戈有拿起几张地契,“珠宝铺子也不少,可有几处是京城中太太小姐们最爱去的?能送进宫中得贵人赏识的又几件?姑娘家置办嫁妆能挑出几件称心的来?”
他说起生意,眼神不再像先前那般沉甸甸,顾盼神飞,语气也咄咄逼人起来。陈寻雁听他说得有道理,也不去计较语气。
一张张价值千万的地契在郑又戈指尖纷飞,被他批得一无是处:“这几家没大问题,经营得却不出色,都是位置出了问题。笔墨铺子安在朱雀门外,太吵,读书人轻易不肯去。新门瓦子的衣料铺子夹在一片酒楼里,谁上酒楼还买衣料?这几家酒楼位置太偏,公子手下有曲院街的好地段,何不布置到那里去?”
“那里酒楼太多,竞争太激烈。”陈寻雁终于有插话的机会。
“酒楼多,商机多,”郑又戈喝了口茶润喉,“难道还怕打不垮其他酒楼吗?”嘴角浮起踌躇满志的笑。
凡事留一线,陈寻雁在心中默念着。
“敢问郑公子,手下管着几家铺子?”
“并无。”话虽如此,可郑又戈脸上无一丝胆怯。
“陈公子,有些能力,是天生的。”
郑又戈使出了他的杀手锏:“陈公子,再看这几家粮铺。铺子都集中在京城,想是粮食都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
得到陈寻雁的肯定答复后,他继续道:“现今黄河泛滥,大运河在五年内必定淤塞。到时候这条商路便断了,公子的布置,可就被全盘打乱了。我是诚心与公子合作,不然也不会说出这番话来。”
陈寻雁心中赞叹郑又戈眼光深远,站起来对着一旁早已目瞪口呆的捡枝道:“给郑公子看茶,前日我新得的明前龙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