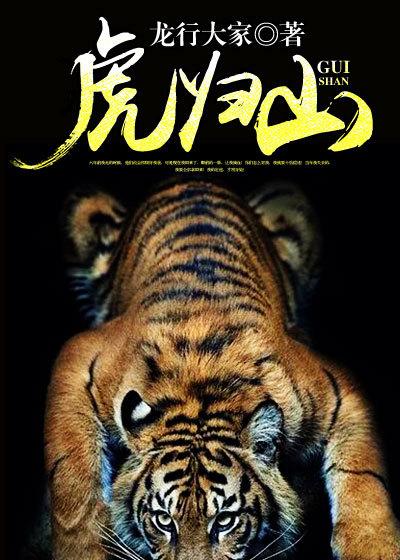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书名前夫攻略 作者九斛珠 > 第14(第2页)
第14(第2页)
半个月后,陈文毅因公事去了京郊。
那晚青姈跟寻常一样,在母亲那儿练字到戌时过半才回屋休息。谁知次日清晨起来,却见陈绍命奴仆围住了那楼阁,说母亲突然得了鼠疫,已不省人事了。
疫症太过凶险,不许任何人靠近屋门,她想去看母亲,却被陈绍命人带回住处锁起来。
很快,陈文毅闻讯赶回,亲自开门去看。
彼时母亲的症状已极重,几乎气绝。郎中将陈文毅包裹得严严实实,到跟前看了眼,很快就被陈绍和奴仆们拽了出去——鼠疫向来极难诊治,传染得也快,尤其是母亲这种急症,人到了濒死的关头,神医再世都回天无力,且一旦传染给他人,京师内外的百姓都得遭难。
到那时候,连累的就是成千上万的性命。
京城两百里外的鼠疫才刚控制住,若这边大意,不慎传入宫中,后果更不堪设想。
陈文毅痛心疾首,却也知道轻重。眼看妻子咽气,带着腹中胎儿撒手归西,沉稳端重的男人跪地不起,生平头回流泪。
陈绍却不敢耽搁,又有闻讯而来的官员焦急催促,说怕疫症传染开伤及百姓,逼着陈文毅下令,拿火油将阁楼泼透,一把大火,连人带屋子烧得干干净净。又将伺候陈氏过夜的丫鬟婆子单独关押起来,说是以防万一。
那会儿已是后晌。
青姈被关在屋里整天,踹不开屋门打不开窗扇,哭得声嘶力竭。
好容易等陈文毅来开门,父女俩衝到荷池边,映入她眼中的只有滚滚浓烟里衝天而起的大火,刺得人眼睛疼。她哭喊着想见母亲,却被陈文毅死死抱着,父女俩跪在大火跟前,就那样跪到次日清晨。
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浇灭残余的火苗。官府亲自派人上门,装了十几车的土将灰烬深埋起来,堆成一座山丘。
青姈连着好几天高烧,就那样失去了母亲。
后来陈文毅想追查源头,又谈何容易?
陈氏的起居饮食都一如往常,临睡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亲女儿,在外间陪同过夜的人又都没有任何破绽。问来问去没半点头绪,隻以为是前几日去进香时不慎碰上了京外鼠疫处来的人,孕妇身子弱,才会被传染了疫症,死于非命。
直到青姈临死,她才得知那晚曾有人进过母亲的房间,换走了贴身之物。
那贴身之物,据青姈推测,必定是枕头。
新放的枕头里藏着鼠疫区的死鼠,一路包裹得严严实实,到母亲枕边才剪开。
那晚房间里还被吹了迷香,无人察觉动静。
直到次日天蒙蒙亮时,白氏借着担心婆母的名义推门嚷嚷,众人才知母亲染了鼠疫。
白氏不通医术,她只是远远看了眼,见母亲高热下脸颊红肿,便断定事情已成,将局面交给陈绍后,立马回屋换了衣裳烧干净,请郎中开药以免差池。陈绍拿着为大局着想的借口,拖着病情不许人靠近,散尽了迷药的味道,等陈文毅赶回时,母亲已是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