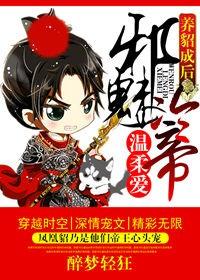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长命万岁讲的什么 > 分卷阅读220(第1页)
分卷阅读220(第1页)
,躬身拿起置于礼服上的小囊。欲转身离去的时候,忽然看到在男子的七章衮服与冕冠中间夹着缣帛,虽被卷束着,但隐约可见上面洇出的墨迹。妇人抬手令随侍停下动作,好奇拾起,低头看起来,她的呼吸渐渐放慢,最后竟觉得咽喉有物窒塞,不能自通。想到不日前女子与她激昂发言的那些陈辞,李夫人摇头嗤笑。已经成长为女君的人,为何还如此幼稚愚惑。从日中开始,天气如火益热。跪侍在左右的媵婢执着长柄腰扇,奋而生风。青铜鑑里的坚冰则使炎风变冷。嘴唇白皱的谢宝因抓着漆几的指节因太过使劲而泛着白,发髻也因挣扎而杂乱,亦已失去开口的力气,而为止痛,她死咬住自己的手掌,最后血珠染红贝齿。李夫人怀揣着心事,缓步进到室内,见女子咬手,不疾不徐的打开小囊,从里面拿出两枚边缘未被打磨过的贝壳,再缓缓屈足,双膝落在席上,然后握过其右手,把子安贝郑重放于她掌心。在谛视良久后,无奈哀叹,起身踱步离开。稳婆还跪在莞席尾端,尝试用手将孩子推回原位。但还未成功,谢宝因却忽然没了声音。妇人意识到什么后,恐慌的抬头去看女子,发觉其气色似绢皓白,意志在衰颓,肌肤被盐汗所覆,气息也在以最缓慢的方式渐渐消弱,使人难以察觉。唯有看似最柔弱的细指依然还在紧握着子安贝。在祈盼母子无恙。稳婆怔松片刻,惊惶出声:“谢夫人?”谢宝因眨了眨眼,眼泪滑落进发间,意识已经接近模糊,她嘶哑低吟道:“阿娘,我头疼。”头疼、血沸、发热、昏睡稳婆随即明白此乃热产的证候。惊悸不安的妇人立即在漆盆中洗去手上血污,然后撑地站起,疾步走出居室,朝中庭前的奴僕大声而问:“医师何时能来?”为避免热气逼迫,室内只留有奉冰奉水与奉风之人。媵婢上前应答:“已经派遣四个奴僕前去,但不知为何,全部未归。”从日出至如今晡时。玉藻归来,闻言望向产室,想及清晨女子所言,自己理应侍在这里使其安心,但如今已是迫不得已,在有所决断后,她将取来的野参交给同从谢氏而来的媵婢:“我亲自去,你们将其切片让女君口含,且绝不可远离女君,必须侍立左右,情况若危急,以女君为重。”媵婢知道自己永远只附属于室内那人,诺诺应声。见此情状,稳婆稍安心,转身要回居室的时候,忽有侍婢冷然出声:“请停步。”待看见为首的妇人,她恭敬的拜手行礼。李夫人几步慢行至门户处:“情况到底如何?”
稳婆如实相告:“谢夫人同时遇上横产与热产,除却孩子难以出来,谢夫人也已经丧失体力,最危急的是养水已泄,倘若再不能诞下,孩子将可能殒命腹中,届时便需要二中取一。”思及前面所看到的那封帛书与前日医师所言,李夫人概叹一声,并无情感:“此乃博陵林氏之嫡长子,必须保住。”但前面名唤玉藻的媵婢却所言非此,稳婆因而陷入疑惑纠结。李夫人松开身前相叠的手,掌心朝上,低头看向这双手,一双曾扼住亲女喉咙的手,她一笑,却是心狠的先兆:“这也是谢夫人所托于我。”若此女被遣返回谢氏,自己往昔数十载岂不皆徒劳。【?作者有话说】【★】横产、热产等相关生产知识都出自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1]恒星:中国古代称二十八宿为“恒星”。亦泛指常见的星宿。→《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公羊传·庄公七年》:“恒星者何?列星也。”[2]此段史料来自魏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魏书华佗传》。[3]出自周??姬昌的《周易·乾卦》。→【译文】初九:龙星秋分时潜隐不见,不吉利。九二:龙星出现在天田星旁,对王公贵族有利。九三:有才德的君子整天勤勉努力,夜里也要提防危险,但最终不会有灾难。九四:有些大人君子跳进深潭自杀,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失。九五:龙星春分时出现在天上,对王公贵族有利。上九:龙星上升到极高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征兆。用九:卷曲的龙见不到头,是吉利的兆头。[4]《礼记·曲礼上》曰:“龟为卜,策为筮。”[5]蓍草【shicǎo】。古时卜用龟甲,筮用蓍草。[6]衿鞶【jpán】。系于衣带上用于佩饰盛物的小囊。→春秋战国《仪礼·士昏礼》:“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之衿鞶。”去母留子2媵婢执扇生的冷风拂过青铜鑑内的坚冰,至于莞席所卧的白皙面容之上,但始终未感到丝毫清凉。及至室外廊廡的声音入耳,谢宝因才有宛若坠落千里深潭之感,身体战栗不息。她细细抽着气,紧握的五指也缓缓松开,掌心的两枚贝壳终于得以见日,而白贝边缘已沾染上鲜红的血迹,白嫩的肌肤也被损伤。活于俗世二十二载,最想要自己丧命的终究还是生她的亲母,原来这就是《道德经》所言的“慎终如始,则无败事”[1]。那人从徠都未曾有所改变。谢宝因像只重伤至濒死的幼兽,出息微微,鼻怠倦的耸动着,却不见眼泪滚落,而被盐汗弄失的长睫再也不能颤动,犹如千钧之重所压。昔日脖颈被扼,口鼻皆不能呼吸的窒感也在渐渐将她蚕食而尽,她指尖无力的往里勾了勾,想要再握贝壳,但仍是不能遂愿,最终无奈放弃。须臾之间,双目合上,思绪也至此由狭长的甬道追述回少时。小小的女郎戴着花树金步摇冠,跽坐在高柳之下的蒲席上,手捧着沉重的竹简,艰难诵读阴阳家经典。以严厉为名的美妇就立在书案前,眼睛望向他处,静静聆听其音,如遇深湛之处,女郎不能即刻诵出,她便会蹙额朝几案看过去,疾言遽色的憎恶而言:“愚蠢之人,果然仅有药石之用。”未满三岁的女郎畏恐的轻放书简,不敢弄出声响,而后熟练低垂下圆润的头颅,年幼的她已经明白,只有家中阿郎来时,阿娘才会欣喜,但阿父几乎不来。于是承受日复一日的恶言,成为平常之事。在这些苦痛的岁月里,她将所有冀望都寄予于百家经典、史书旧章以及山水之文,如此才能快乐无已,而后众人皆称赞她弱龄早慧,幼学夙成,再是“诸生”。及至五岁,寒冬某日的清晨。美妇突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