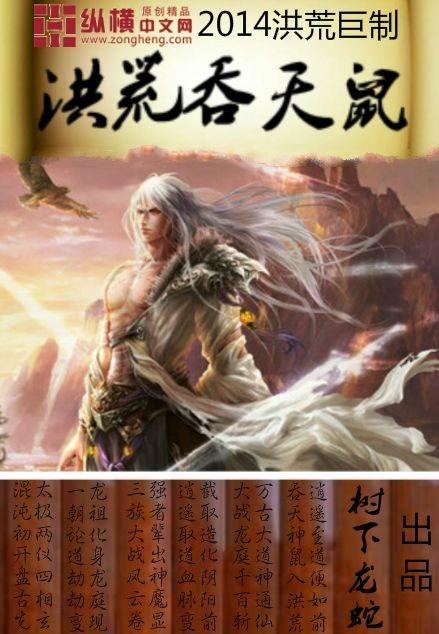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离亭宴煞古诗诵读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他抬头看到她柔化的眼神,当她在心疼衣裳:“看来你还是偏爱红色,这些年虽不见你穿了,可我知道,你是喜欢的。既如此,回去叫人修补便是,我常穿给你看。”
见他会错了意,萧清规摇了摇头,指着他手背上的伤问:“该伤的不是吕琮?你这又是怎么添的?”她明明记得昨日还没见到,刚刚他斟酒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了,只是现在才说而已。
萧翊错愕了一瞬,闪烁而过的迷茫像是自己也不知道似的,语气如常道:“我只为打断他的腿,何须与他过招,更别说伤我,许是磕碰到了。”
他的伤看起来绝非寻常的磕碰,萧清规知道他不愿实说,也不再追问,默了半晌终是没忍住,主动拉了他的手,抚上面的伤:“擦过药没有?”
“擦过了,明日便会好。”
这话又是诓她了,今日添的新伤,哪就好得那么快了?
萧翊换到她右侧,转而去牵她的右手,左手已经被他焐热了,他向前走,却发现她还站在原地,欲言又止似的看着他。
“那会儿在院中赏月,并非是听真颜抚琴入迷,而是想起往事,出神了片刻。”萧清规低声说道。
“猜到了。我在院中站了许久,直到金铎响了你才回头。”
提及往事,萧翊心中也不免一紧,只是不知他们心中所想的可是相同的往事。
萧清规踯躅许久,久到右手都被他握热了,才带着一丝哀戚开口:“寿眉常说,皇兄是整个宫中待我最好的人,她说得不错。可即便你对我这般好,我竟还会时不时怨你、恨你,你可知为何?”
萧翊此时确信,他们想起的往事不尽相同。这下轮到他不说话,等待她开口,仿佛落下行刑的斩刀。
“你还记得我少时想学长乐舞,可自从出了凉秋宫,到我沦为废人,足有半年的时间,我却丝毫没有学过,你岂会不知为何。我在凉秋宫等了你四年,那时我才十岁,你却始终没有再来,我一直记着。”
那时他便告诉过她,萧玉华虽然对他很是爱重,可他自己心中清楚,他的亲生母亲想必是个北朔女子,大抵萧复还未复国之前留情所生,萧玉华又多年无子,心性良善,才将他收入宫中。
幼时他是极不学无术的,为此看过很多北朔的史实或异闻,对北朔的了解很深,萧清规知晓长乐舞也来源于他。
记得凉秋宫中的最后一面,他给她带了一把三石长弓,彼时的萧清规丝毫都拉不动,长乐舞也只教她了个起舞的姿势,便是用双手比作玄鸟,于空中纷飞。
她经常爬上墙垣,从天明等到日落,在夕阳的残辉下翻手比出玄鸟,将玄鸟放飞到宫墙之上,淹没于无尽的等待。
萧翊全然无从辩驳,只能如实说道:“元徽十三年,东夷尚在,江南边界民情不稳,我向父皇主动请命,出任江州总管,一去就是两年。元徽十五年,江南稳定,我回京述职,向父皇请赏放你出凉秋宫,父皇震怒,在京停留不过三日我便又回了江州。元徽十七年,平定江南水寇,我带着军功回京,不曾想你已经出了凉秋宫,还给了我个意外的惊喜。阿菩,你可还记得,少时我不受父皇重视,宫人也敢随意欺凌,是你指着刚学的诗文告诉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我是为了你才开始夺权的。”
这些要被编撰到史纲中的事情她岂会不知,可她只是不能理解:“那你为何就不能告诉我一声?你可知等待的滋味有多煎熬?”
“我知。”他言辞笃定地先答了她后一句问话,才继续解释,“我确实是故意不告诉你。你怨我、恨我,我都接受,但我不后悔。我就是要你等着我,这样你才不敢忘了我。”
萧清规忽然觉得蓄满力的拳头都打在了棉花上,他无耻得过于坦荡了。
她有些负气地立在原地不走,萧翊平复了心绪,含笑问她:“走累了?我背你。”
萧清规就近找了个石阶坐下,显然是拒绝了他的提议,萧翊也不强迫,随她一起坐下。危燕台的高度虽不足以俯瞰整个皇宫,却足以看到最为威仪的离亭,肃穆地屹立在夜幕中,审视着永安。
两人看着远方,萧翊幽幽开口:“阿菩,现在就很好,我陪着你,你伴着我,这个皇城就变得有意思得多。我们就这样……”
他还没说完“度此余生”四个字,发现萧清规转头看他,他们离得很近,就像登了半程燕归山就离天上的月亮近了许多似的,他恍惚间以为眼前这尊明月唾手可得。
萧清规将他打断:“皇兄,我还能像过去那样,靠在你的肩头吗?”
他不答话,直接伸手将她的头按上自己的肩膀,仿佛在说:有何不可?
她就那么躺在他的肩头睡着了。萧翊独自望着远方的离亭出神良久。
元徽二十四年,萧复驾崩于太极殿。彼时他和萧旭远在曲山皇陵祭祖,还有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萧恪。萧恪年长萧旭三岁,早有夺位之心,当时在宫中的清规以身作旗,一袭红衣亲登离亭,向他的暗哨发出信号,他亲自带萧旭连夜回京。全靠他们兄姐二人力保,萧旭才能够坐上如今的皇位。
那便是她最后一次穿红衣,他虽未能亲见,多年来无数次想像,胜过亲见。
追忆红衣的清规,他又想起马场中她驰骋的样子,凉秋宫最后一次见面,他送她一把三石长弓,本是打算亲自教她射艺的,可机会来得太过突然,他不得不抓住,等到他从江州回来,她已经出了凉秋宫,也可射三石之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