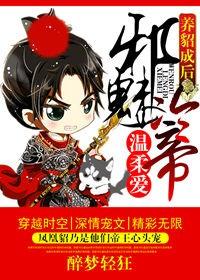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深海鱼油什么时间吃效果最佳 > 第33页(第1页)
第33页(第1页)
可我唱不出来了,中文我唱不出来了,明明我唱过,我张嘴哼了半天调子,一出声却不知怎么唱了,我气恼的拍拍轮椅的扶手。
其实我不需要坐轮椅,就是有一天吐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晕过去,院长从此赏了我两个轮,这可太好了,小马扎勒的我屁股疼。
我闭着眼,重新去想,哼着哼着就睡着了,我躺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
好久不见的江岸来看我了,他如今30岁,可他没有穿西装,牛仔裤配了一件黑短袖,像十八岁的大学生,不,比大学生好看的不止一星半点,虽然大学生没做错什么。
他拨了拨我的刘海,我的刘海都是我自己剪的,当初被火烧断后头发都不爱好好长了,我天天拿着树叶蹭,蹭了一年才想起来长头发的不是树叶而是生姜。
他把我从轮椅上抱起来,那三只傻子在边上不知所措,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他那一身的杀气依旧没有褪去,三只傻子闭嘴了。
“小潭,我们回家了。”他说。
他抱着我下了坡面,走出了这个庭院,他的怀里温暖如春,我在睡梦里勾了嘴角。
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了浮雕的吊顶,我又合上眼去,我想看仔细些,我想把病院里的宿舍也雕成这副模样。
我闭眼看了很久,其实我早就烂熟于心,我蒙着眼用嘴刻也能刻出来。
然后我睁开眼了,可我还是看到了浮雕的吊顶,沼泽地待太久会陷下去,我想走。
我发狠地掐着自己,可我还是梦魇了。
门被推开了,我听到了很轻的脚步,然后我看到了江岸。
“你醒了?”
他像没料到我在这里一般。
“我睡着。”我说。
他坐在床边,摸摸我的额头,“小潭,我们已经回家了。”他说。
我把自己缩起来,用被子蒙住头,“我没有家。”我说。
身上重了些,江岸隔着被子抱住我,“生我的气了吗?”
我觉得今日的梦奇怪了些,莫不是有鸟趁我睡觉在我脸上拉了屎。
“生叔叔的气了吗?”他坚持问我。
“别捂着自己好不好,会气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