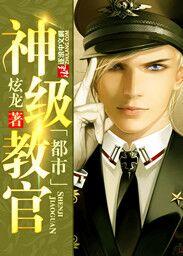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宫女在逃八月樱桃笔趣阁 > 第34章 第 34 章(第1页)
第34章 第 34 章(第1页)
次日,殊丽回到尚衣监,就见晚娘坐在耳房内,像是等了她许久。
殊丽没精打采地躺在老爷椅上,随口问道:“不生气了?”
晚娘掩好门窗,流露出憔悴,“跟你说件事。”
殊丽“哦”一声,早已猜到她是为何而来。
晚娘坐在边上,小声道:“我和老谢的事,怕是被人发现了,他说要去御前替我二人求情,再选个吉日迎我入门。”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殊丽漠笑,头一次用冷漠待她,“你若觉得谢相毅值得托付,就去孤注一掷好了。”
晚娘没想到好姐妹是这个态度,“你还在跟我置气?不是,都什么时候了,我跟你讲真的呢。”
“讲真的吗?那好,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谢相毅贪色卑劣、油嘴滑舌,别说娶你,不将错全部推给你就不错了。”殊丽翻身背对她,冷笑一声,“到时候,他只会说是被你引诱,一时犯了糊涂,错全赖你。你当他是全部,他却把你当作瓶里的一束野花,连收藏的价值都没有。”
在晚娘的印象里,殊丽从来温柔和善,哪里讲得出这样的话语,可谓字字刺耳,句句残酷,痛得她无法呼吸,“你没经历过,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你走吧。”
晚娘惊讶地看着她,伸手去探她额头,“你是不是病了?”
殊丽挥开她的手,“若你还信我,从此以后就与谢相毅划清界限,若不信我,请便。”
贪色之徒,哪里来的真心!
晚娘一时无言,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谢相毅的看法出了偏差,“行了,你歇着吧,我不打扰你了,若有命活着,我再来看你。”
“来向我告别的?”殊丽坐起身,盘腿坐在老爷椅上,“可你知道么,木桃因为你,失去了提前出宫的机会。”
“!”
两人不欢而散,更确切地说,是晚娘颓然离场。
夜深人静,殊丽写了一封信,交给宫里门道极多的宦官,让他将信送到元佑手中。
有些事,与其不厌其烦地规劝,不如让当事人亲耳听到,只有切肤之痛,才会彻底醒来吧。
而这件事,殊丽不敢去劳烦天子,只能与负责此事的元佑周旋,虽然不待见元佑,但能使上力的,只剩元佑。
隔日晌午,青色官袍的男子如约来到了冷宫前,他抱臂站在树荫下,看着殊丽慢慢走来。
烈日灼灼,树荫下倒是阴凉,可殊丽宁愿站在灼阳下,也没有靠过去避暑的意思。
“陛下将谢相毅的事全权交给你,想必不久之后你就会处置他,我需要你帮我一件事。”
“跟人谈条件就这态度?”元佑用刀刻着一块木雕,没抬眼看她,“再说,这等小事,还需要我出面?”
这事不就归他管么,怎么还想着撂挑子了?天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殊丽沉住气,不想被他牵制情绪,“开条件吧。”
元佑看过来,像是决定为她破了一次例,“万寿节后,我要去榆林镇探望义父,你随我一道。”
去见二舅舅
殊丽干脆点头,“好,你来说服陛下。”
以天子的脾气,不削掉他的脑袋才怪,正好借刀杀人了。
殊丽忿忿地想。
元佑笑,“成交。”
没几日,元佑带兵包围了谢府,拿下了谢相毅。
当时,谢相毅正在府中买醉,手里拿着银鞭,一下下鞭打着自己的小妾。
当元佑出现时,小妾们胆战心惊地看着这个天降的青衫男子,被男子冷眸一扫,纷纷跪地求救。
元佑嫌麻烦,直接让人将谢相毅捆去了谢府书房。
他从书案下面勾出一把椅子,叠腿坐在上面,拨弄起笔架上的长峰狼毫,“谢相毅,本官奉旨审问你些事情,你若支吾其词,休怪本官用刑。”
那点酒气早就烟消云散了,谢相毅知道元佑因何而来,赶忙跪地:“但凭元大人问话。”
他额头抵地,满脸不忿,可被人抓住把柄,再难受也得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