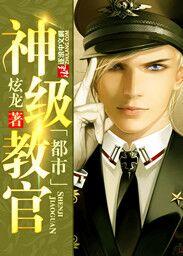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绿天庵拼音 > 第44页(第1页)
第44页(第1页)
淳儿回来的时候,穿着一身孝衣,长生第一眼看过去时,觉得很是晃眼,便无声无息地倒下去了。
秦牧几乎是发了疯地逼郎中想办法,可这一次,再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留住他了。
除夕夜,长生回光返照地自己坐了起来,把淳儿叫到身旁。
淳儿不敢痛哭,强忍着跪在床边拉住长生的手。
长生温和地看着他道:“你长大了,以后你母亲和弟弟都要靠你照拂。”他让淳儿从柜子里找出一个沉甸甸的木匣,打开来,对他道:“我这些年的积蓄都在这里,原本是想等你父亲回来,给他重新置买宅院的,如今,都交给你了。”
淳儿泪如雨下地点头。
长生替他擦着脸上的泪水,渐渐觉得疲惫起来。秦牧绷着几乎快要崩溃的面孔把长生小心地扶在怀里,让他能稍微舒服一点。长生喘了口气,继续对淳儿道:“我此生一事无成,却性格乖戾,自以为受尽苦楚是成全了你父亲,却最终害了他,实在罪孽深重。我死以后,务必火葬,骨灰全部撒入江中荡涤干净。”
“叔父!”淳儿终于忍不住摇头痛哭起来。
“我只有一件事,”长生觉得胸中渐渐绞痛,淳儿的模样也逐渐变得模糊,他喘了口气,努力指着墙角放着的两个木箱道:“把这两箱东西送回山庄,去绿天庵找一个盒子,一起葬在山上。”
“绿天庵?”淳儿哭着问道:“找什么样的盒子?在什么地方?”
长生痛苦地按住胸口,“绿天庵,后院,有一棵古槐,盒子就埋在树下。”
淳儿连连点头,握住长生的手哭道:“淳儿记下了。”
长生歪在秦牧的怀里,闭上眼睛,眼角落下一行泪,他慢慢伸出手去摸秦牧紧紧箍住自己的手臂,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不知是忘了我吧还是放了我吧的话,手就缓缓地垂落下来。秦牧佝偻着身体把长生死死抱在怀里,发出一阵让人不忍闻的低吼……
窗外莹莹地飘洒着鹅毛般的雪片,在新旧之交的这个夜晚显得格外安详静谧。
☆、噩耗
正月里,皇上驾崩,举国哀悼。一个月后,新帝继位,大赦天下。
长生死后,陶淳没有回家,一个人住在卧佛寺里,一来,他已经在寺里住了十年,早已习惯和长生在一起的规律生活,二来,他知道母亲并不喜欢他为长生日日上香,只得把长生的牌位放回寺里去。旁边书院里的老先生,过年回来惊闻长生去世的消息,很是哀痛,哭了几次,勉力陶淳努力学业,将来定要金榜题名不辜负长生这些年来的苦心。
秋日的一个下午,陶淳正在书院里温习课业,弟弟突然无比欢喜地从家里跑来找他。
“爹回来了!”陶谦摇晃着一脸呆滞的哥哥在他耳边高声叫道。
“你胡说什么!”
“是真的,就在刚才,爹回来了!”陶谦说着,一把夺过哥哥手里的书,拉着他一路跑回家里。
陶淳上气不接下气地跨进院子,看见母亲正欢天喜地指派几个侍女收拾书房。芸娘扭头看见陶淳,立刻让他去内院正厅里拜见父亲。
陶淳觉得一阵腿软,哆嗦着朝内院走去。
厅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依稀是陶淳记忆中父亲的模样,只是沧桑了太多太多。陶淳几乎僵硬着身体慢慢挪进去,嚅喏着叫了一声“父亲”就跪下来泪如雨下。
陶祝哽咽地抱住陶淳,只一味点头,几乎说不出话来。
芸娘兴高采烈地除去家里的孝布,让家丁把厅里供着的牌位赶快拿出去劈了,亲自下厨准备了诸多好菜。
陶淳泪眼婆娑地望着父亲,“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消息说你去世了?”
陶祝感慨地叹了口气道:“去年,我在采石场被滚落的石头砸伤,被人送到医馆里,因为跟着郎中,所以幸而在得病之初就对症下药,算是捡回一条命。后来边州乱了,我只好跟着郎中和幸存的流民上山避疫,直到疫情过去才又回到拘所,官差知道出错,怕被追查,也没有再更正名单,说新皇既已大赦天下,让我自行回乡。”
陶淳听了连连感叹,他望着父亲,经历这么多年的苦难,他仍旧是记忆中慈爱温和的模样。
芸娘在客厅里摆了整整一桌子菜,让两个儿子和几个家丁侍女一起陪着吃了期盼十几年的一顿团圆饭。
陶祝慢慢咽着口里的饭食,几次想要问长生的事,却都被芸娘岔开话题,只好默默忍到吃完这一餐。陶淳在一旁看着,对着眼前的饭食几乎难以下咽,他草草地吃了几口,悄悄退到庭院里去。
陶祝走到院子里,十几年不见,他对这个家已经觉得无比陌生,却只对淳儿莫名地感到亲切。他犹豫着,胆怯地拉住徘徊不定的陶淳,满怀期望地轻声问他:“淳儿,你可知道你叔父如今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