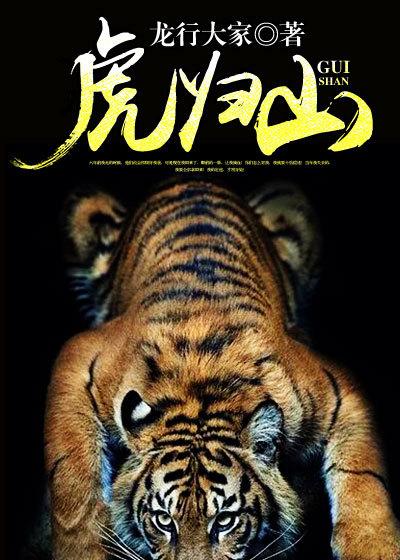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江山笑是什么歌曲 > 第178章 长明宫(第1页)
第178章 长明宫(第1页)
大齐,长明宫。
瓦檐上滴落着涟漪的雨珠,冷清清寂的内殿,微黄的烛火黯淡着,却装满了空旷巍峨的长殿。
宫中的夜,是极静的。
已是五月,此刻大齐最巍峨的宫殿内却充满了寂静与清凄,只有不时传出的几声清沉的咳嗽声。
“咳……咳咳……”
殿外守夜的宫人路过长明宫时,都在远处轻轻摇着头,小声道:“听说君上病得严重了,这些月长明殿像是空点着灯,君上大概为了避人耳目,没住在这吧?”
“这些日,君上开始上朝了,长明殿也无故多了咳嗽声,难道君上好了不少?”
“哎……快走吧,宫中千万别议君上的是非。”
“……这不是忍了几月了吗?”
殿内,顾听桉那张惊为天人的面庞苍白得宛如白纸,他半靠在床榻上,微垂着眉眼,冷白的脖颈胸膛处皆残留着抓挠的红痕与青印。墨染的青丝垂在肩头,越发晕染出那份无力的苍白。
像一朵半开的月下昙花被人摘下,最终漂泊在无定的溪流中。
卜忆半跪在顾听桉床前,深暗的眸透着淡淡的担忧,“主子,您……明日还是让小殿下代朝吧。”
“阿行还小。”顾听桉修长的手中紧攥着一张白帕,他低头看着上面隐隐的血迹,淡淡道:“时间来不及了。”
卜忆一向冷沉的音色中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不,来得及。纪老说了只要主子安心静养……五年之内,主子都可无虞,况且夫人带回的那张药方只差了一味了……”
顾听桉闭眼摇了摇头,“复白草,你们找不到的。”
在顾听桉的记忆中似乎出现过这株药名,他记不得了,可他却知道这个世上不会再有这株草药了,“况且,苟且偷生的五年,我不要。”
日日沉睡,醒来便是苦涩的药汤,拖着残躯苟活,此般生不如站着死。
卜忆道:“不试试,主子又怎会知道呢?况且主子不念着自己,也该念着夫人……您总说她一生坎坷崎岖,要作她手中披荆斩棘的利刃,最后又怎忍心留她一人孤独于世?”
顾听桉想到记忆中已快要模糊的青颜,心尖忽地一颤,竟是比心脉发疾时更痛几分。他指尖都攥得那染血的白帕发白发青,最后那深藏的疼痛却终只是被同女子如出一辙的平静压下,他淡淡道:“先生本便是一朵向阳而生的玫瑰,她不需要利刃,亦不惧黑暗,她自身便是荆棘,便是灿烂。”
话落,他幽清深邃的桃花眸似承载着亘古般绵长的海岸,连续又静谧的波涛拍打出轻柔的浪花。良久,他清沉的嗓音平静着,“……我杀了江青寒,注定同先生不再是一路人——三年之内,让天下大齐,这是我唯一能为她,也为我所做之事。”
卜忆听后清楚了,他一向果决帷幄的主子此时竟已做了必死的准备,卜忆的瞳孔都在颤抖,他只看着床脚处那一滩血色,最终只能无力地低声道:“主子想隐瞒这一切,可夫人又哪里不会察觉到什么呢?”
顾听桉沉默了一会,淡淡道:“先生的理性比你所想的强大。待天下大齐,彼时已是太平盛世,她没了责任,也再不用受任何禁锢。而我伤害了她最亲之人,对她避而不见,日日在宫中姬妾成群。先生的骄傲不会允许她回头的,先生一直觉得自己亏欠了沈槐奚,适时他们可以一起回东槐,真正去见识瑰绝自由的山川湖海……”
“那主子呢?”卜忆听后,幽深的面容有些隐忍,“您便不曾为自己着想一分?”
仅说了几句话,顾听桉似乎又觉得累了,他撑着身子躺回榻上,轻喘着气,最终只淡淡道:“天下人来人世一遭,本也无人可带走些什么。”况且,先生这一生都会记得他,已足够了。
“主子从前不是这般,只要有微乎其微的生机,主子都应抓住才是……”卜忆的眸暗暗垂下,“或许……夫人会知道那最后一味药在哪……”
话落,顾听桉寡淡虚弱的嗓音骤然提高两分,“咳咳……凡泄露一分,咳……此消息者,杀无赦!”
“让笑渊和鬼面保护好先生……另外,每三日将先生的情况告诉我。”
卜忆握了握拳,“主子!”
“去各地挑选些有才华的女子来宫中,请容聿来宫中教习她们。”顾听桉心尖很痛,他头脑又渐渐开始混沌,他知道自己反应大不如以前灵敏了,而今又要开始沉睡,他最后嘱咐道:“卜忆,不要让先生知道……你明白,那比病痛更扼我心……”
最后一个音落,床榻上男子深邃的眼眸已闭上,卜忆无力地起身凝着床榻上本该风华无双的男子,最终只为其掖好被角,眸色至暗,“主子,三年来你心中只念着夫人,可您的一生难道就不崎岖幽折吗,小殿下本可在您的羽翼下做肆意权贵,如今却生生要担起整个大齐——她是您的灾难……”
床榻上的男子连眉都未动一下,卜忆没再说话了。转身便融入了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