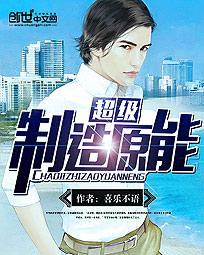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金粉世界电视剧百度百科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人心变了,戾气十分,他们的兽性毕露,其昌,我非常的失望。”
“我早说过你,热情的人容易失望,这是必然的事。”
“其昌,同时我也觉得累。”
“天天工作廿四小时,想不累也不行。”
“其昌,我决定休息一下。”
我心一动,莫非时机已经到了?
“我告了一年的假,停薪留职。”
“呵,天大的喜讯。”我雀跃。
“我们可以结婚了。”
就这样我们便乐洋洋的筹备起大事来。
不是说笑,多谢张碧琪,要不是她摆出一副堕落得烂心烂肺的样子出来,我的慡慡对她那伟大的事业尚念念不休。
我们在一、两月间便办妥一切。
新居、新家俱一应俱备,我为这头婚事早已准备了年,婚后其乐融融,慡慡不再出去跑新闻,只在家撰些杂文稿,空余时间把一头家打理得整整有条。
有一天下午,她说:“原来张碧琪被判入女量监禁所一年。”
我冷笑,“她还算女童?”
“其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社会上的渣滓。”
“还有。”
“什么?”我没好气。
“她母亲死了。”
“怎么死的?”我非常震惊。
“原因不详,听说是自然死亡。”慡慡说:“其昌,不一定要在欧洲念大学的女人才可以恋爱,碧琪的父母很相爱,孩子们也很听话,直到他父亲在地盘意外丧生,她母亲才自暴自弃,沦落到这种地步。”
“这不是理由,坚强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生存下去,况且这毕竟还是安泰的社会,只要肯劳动,就可以图得温饱。”
“好了好了,别慷慨潋昂地演说了。”
我叹息。“你看,你的努力全都泡汤。”
“还有。”
“我不要听。”
“这件事你非听不可。”
“我不要听。”
她啼笑皆非,“赵其昌,我有了孩子。”
“什么?”我跳起来,“你为什么不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