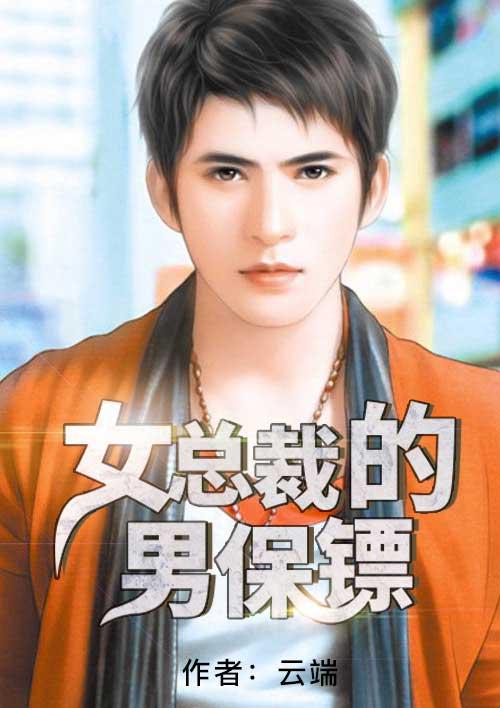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韶华舞流年 剧透 > 第82页(第1页)
第82页(第1页)
提到尊主,琰青的脸上又显出几分敬畏,“尊主是何人子尧岂非比我清楚,我从未见过尊主的正面目,子尧如此相问,倒叫琰青意外了,你与尊主……”说到此处,他不再多言,但祁溟月已从他的话中猜到,自己必定是被当作了父皇的男宠之类,却只是挂着浅笑,并不解释。忽见琰青掌中现出了一枚尖刺,继续说道:“那日抹的只是迷药罢了,琰青从未想害你,只是一时心急,想借你天音之力去救一个人。”“那你便是用错了方法,若是为了救人,为何不与我直说,却要用迷药,莫非你是想乘我昏睡将我带出城,直接去往那人之处?子尧还不知,是何种症状需用天音救治,琰青又是如何知道我使得的是天音?”对着他一连串的问题,琰青苦笑,“而今说这些又有何用,琰青虽已后悔,但做出的事不可挽回,尊主未曾取我性命已是万幸,何谈其他。”在祁溟月眼中,琰青始终是那日所见,带着些慵懒媚意的绝色公子,今日却忽然见到他如此的笑容,其中的苦涩和悲切,让祁溟月愈发好奇起来。“琰青如何知道,而今说那些已是晚了?若我告诉你,我决意相助呢?”本就对他有些好感,又从未介意上次的事,原本只是疑惑,但在听了他的话之后,祁溟月倒是真想知道其中的究竟了。“你愿相助?”琰青露出了意外的神色,想起那一日尊主的怒意,他的脸上又显出了几分迟疑,“即便子尧愿意救他,但尊主不允,也只是空话罢了。”瞧了一眼安坐一旁的祁溟月,他那飞扬的眉,含笑的唇,还有舒缓悦耳的语声,眼中如水的沉静,一言一行,无不引人心神,让人忍不住陷落在那温润的气质之中,如此风姿无双之人,也莫怪久不现身于江湖的尊主,会将他看的如此之重。可经过上回之事,尊主如何还会答应让他相帮自己。摇了摇头,琰青垂下眼来,半刻没有言语,待他再抬起眼,眼眸之中只剩下了某种坚决,神色郑重的开口说道:“即便尊主不允,琰青也要求你一事,求子尧帮我救治一人。”见他如此执着的想要救他口中之人,祁溟月猜想,此人必定对他十分重要,口中并未相询,他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琰青见他答应,似乎松了口气,恢复了原先从容媚惑之姿,随意的往后倒去,懒懒的靠在了椅上,合着眼,似乎坠入了某种回忆里,“想求子尧相救之人,我已许久未见了,距上一回见他,已有五年……”琰青的语声本就如梦中的呢喃低语,此时更是多了些飘渺,祁溟月只听那如叹息般的话语继续说道:“五年未见,近日我却突然得知,他不知为何沉睡不醒,已一年有余,全靠汤药续命,连闻名于世的医毒伊家都束手无策,只知是某种蛊毒,却无法可解,除非让它自行离体,不然便只有等着他沉睡致死的那一日。”叹了口气,他眼神注视着祁溟月,“据伊家所言,此蛊只会使人沉睡,药石无解,除非找到那下蛊之人,不然,便是天音,只有练到极致的天音,方可任意控制蛊毒,而不必担心寄主的安危。早先尊主身边有一女子,据说会使天音,可惜尚无法使天音随心而动,那时琰青便知道了关于天音之事,后来那日偶然路过酒楼,听到子尧所奏,那相似的乐声,恍如天籁,却无人因此失去神智,我便知道,擅使天音之人终于被我寻得了。”其实之前他也曾闻凌山之上有过所谓的魔仙,便知道是擅用天音之人,那时并未对此在意,而后家中那人出事,想要去寻,却已是来不及了。又是蛊毒?祁溟月听琰青所言,微微有些惊讶,之前是连心蛊,这回不知又是什么?“天音确实可驱蛊毒。”待他说完,祁溟月肯定的对他说到。虽知确实可行,但心中犹有些不安,怕未必如伊家所言,此时听了这话,琰青顿时放下心来,不知为何,眼前才刚是及冠之龄的少年,却让他莫名的觉得信任,“子尧既然这么说,我便放心了,只是上回之事,仍觉歉意,望子尧莫要怪罪。”祁溟月摇了摇头,“既然已经过去,又何必再提?在子尧眼中,琰青便是琰青,只会有勾魂媚人的万种风情,绝不适合露出如此的歉意,若你像上回一般,子尧兴许还习惯些。”琰青连忙摇了摇头,“琰青已知子尧绝不是可随意挑弄之人,若被尊主知晓,恐怕……”轻抚一下胸前的伤处,琰青想起上回的事仍心有余悸。“你还未告诉我,何谓尊主?诩……便是你口中的尊主?”听他说起,祁溟月顿时想到了还有这事未曾问他,不知父皇在江湖中尊主之称有何而来,琰青又是负责何事,现今是否仍听他号令。已经唤了尊主的名,却不知其他?琰青诧异,“尊主当年在江湖中,可是有暗皇之称,连朝廷都拿他没有办法,子尧竟会不知?”暗皇?听到这个名号,祁溟月不知该露出何种表情,面上顿时有些古怪。往日的暗皇便是今日的帝王,若被江湖中人知晓,不知会作何反应。对峙答应了琰青救人之事,祁溟月回到宫中,无爻已归,隐在暗处的气息似乎与往日没有不同,但不知为何,祁溟月却觉得他更虚无了些,有些心不在焉。记起在流芳馆门前察觉的那道视线,还有那转身离去的背影,再加上无爻近日的不对劲,若说其中没有关联,那是绝不可能的。心中有了猜测,但却不曾相问,总如幽魂似的无爻,偏偏让祁溟月有几分说不明的信任,不愿随意探询他的过往。放下对无爻的担心,祁溟月想起答应了琰青的事,不觉有些头疼如何与父皇交代,看看天色,祁溟月去整了衣袍,往御书房行去。一路上的宫人侍卫一个个向他行礼,口称太子殿下,让祁溟月颇有些不习惯,自他被立为太子,别人对他的态度便愈发恭敬,但于他来说,自觉周围并无变化,他的衣食用度本就与父皇的一样,而今虽是太子,也不过是照旧罢了。随着一路的请安问候,祁溟月来到了御书房的门前,门口自然守着无数不少的侍卫,不过却不见刘总管的身影,想来应是在里头照应着。才站到门前,有侍卫见他到来,连忙行礼,而后便想要朝里面通报,却被一旁的另一侍卫给悄悄扯住了衣袖,朝他使了个眼色,不等他反应过来,便为祁溟月打开了门。在宫中时日久的都知道,当年陛下对二皇子是如何的宠爱,只要是他想去的地方,无人可以阻拦,若是二皇子要见陛下,不论何时何地,都只管放行便是,如今二皇子归来,不止让受着恩宠的三皇子成了阶下囚,更是被陛下封为了太子,虽过了些年,但如今看来,陛下对他的宠爱却并未少了半分,仍旧如当年一样,是众位皇子中,唯一得到陛下宠信的皇子。看看别的几位,陛下也就只是隔三差五的问个两句,哪能与二皇子所受的恩宠想比?在这帝宫之中,可以说,除了陛下,便是二皇子,也就是如今的太子殿下的身份最为尊贵,他们这些身为侍卫的,若不懂得察言观色,说不准哪一天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为的什么。扯过一旁犹在疑惑的同伴,那侍卫开始了一段长长的训诫,开始将太子殿下当年的往事一一细说。这一边,祁溟月听到身后传来的话语声,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些时日以来,听着无处不在的私语和传言,他终于觉得自己确是回了宫了。踏入御书房内,眼前仍旧是他熟悉的摆设,香炉燃着熟悉的冷香,和父皇寝宫内的一样,书案旁,刘总管静静候着,仍是一贯的面无表情,父皇正懒懒的靠坐在椅背上,看似随意的在奏折上书写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