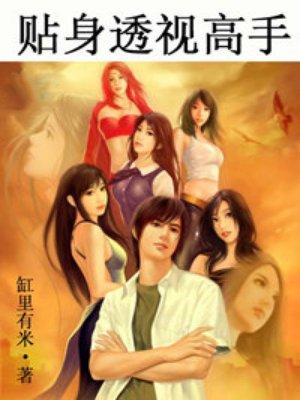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普鲁斯特墓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ldo;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rdo;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ldo;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rdo;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ldo;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rdo;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ldo;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rdo;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ldo;航船&rdo;,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ldo;东极号&rdo;,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ldo;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rdo;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ldo;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rdo;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ldo;悲伤&rdo;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ldo;炮仗狗&rdo;,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ldo;就送到这里了。&rdo;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ldo;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rdo;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ldo;井&rdo;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ldo;老鹰捉小鸡&rdo;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ldo;母鸡&rdo;。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ldo;炮仗狗&rdo;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