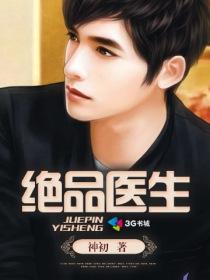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苦海无涯苦作舟下半句怎么说 > 14 爱(第1页)
14 爱(第1页)
薛汶撑着伞,和薛怀玉并肩来到a区36排。
雨水把形式各异的墓碑冲刷得一尘不染,一束挨着墓碑摆放的鲜花被这场滂沱的雨打碎,花瓣凋零地落在地上,随着积水被冲下阶梯。
他们穿过走道,最终停在其中一个墓碑前。
碑上用红漆填涂的名字和生辰已经在风吹日晒中褪色,只剩凿下的笔画苍白地留在石头上。他们无言地站在原地许久,雨水的湿气慢慢浸透了身上的衣物,黏在皮肤上。
就在薛汶想着是不是该说点什么的时候,薛怀玉终于开口。只听他说:“哥,你们很像。”
雨声差点把这句话淹没,幸好他们站得近。
薛汶转头看了薛怀玉一眼,一开始没能反应过来“你们”是什么意思,但很快他就愣住了。当他再次看向眼前的墓碑时,薛汶忽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躺在这地里的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
他那平生素未谋面的亲生父母。
“你们”指的是他和他们。
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顿时涌上心中。
其实薛汶早就知道薛怀玉的父母因意外离世了。他们的死亡在下属递交上来的报告里是一句白纸黑色的话,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和原因,简单明了得如同是剧本上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故事情节。当时的薛汶也不过是扫了一眼,从未把这个事实放在心上,更没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有任何关系。
直到这一刻。
被他忽略的关联如雷电般击中他,令舌尖和垂在身侧的那只手的指尖骤然感到一阵发麻,泛出一股焦灼的苦涩。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许久后,薛汶问道。
“他们啊。”薛怀玉说着顿了顿,半天都没有继续下去,仿佛他正在用这停顿的片刻反刍过去的记忆。
要说薛怀玉从小听得最多的话,除了“你长得好好看”以外,就是“你爸妈好好,好羡慕你”。
夫妻二人几乎称得上是所有小孩心里最完美的父母样板。他们温和且开明,愿意去倾听和了解薛怀玉的想法,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和决定,从不会用父母的身份打压孩子,发泄情绪,哪怕工作再忙,也会抽时间陪伴他。
即使是后来薛怀玉年岁渐长,到了同龄人都免不了烦恼于学业和各种社会压力时,父母最常对薛怀玉说的却仍然是那一句话“别想太多,活得开心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活得开心。
薛怀玉不知道怎么才算活得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可以如此爱他。明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处,他们却总能温柔地拥抱他。
他沐浴在别人艳羡的爱意中长大,却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异常。他发现自己没法像别人一样真切地体会并理解人的七情六欲,对于一切的感情都有种天然的冷漠与麻木。
他是手术台上的医生,试图通过理性的解剖去理解人为何会感到悲伤或是快乐,而人又为什么会在幸福的时候流泪,也会在苦涩的时候流泪。
可手术结果是一次次的失败。
薛怀玉开始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藏在他脑子里的疾病,但他没有去查过。而当得知自己并不是父母亲生后,他终于感到一丝释然。
他想,一切的错误都出在他身上。那个过去二十多年来的试图伪装成正常人的自己原来并未辜负父母给予的爱,只是生来就脑子有问题。
“他们是好人。他们非常爱我。”漫长的沉默后,薛怀玉回答了薛汶的问题。
雨还在下。
雨点打在伞面上,震颤顺着伞柄传递到薛汶的手腕上,使得心脏也以微不可闻的幅度在胸腔里震颤,让他感到心悸。
“车钥匙呢?”薛怀玉忽然再度开口,问道。
“兜里。干嘛?”薛汶反问。
那人把手伸进他的衣兜,掏走了钥匙。
“我先回车里。”薛怀玉丢下这句话,在薛汶反应过来之前便转身跑出了雨伞为他们带来的这一小片安全空间。
雨落在那人身上,顷刻间便把外套打湿了。
薛汶喊了一声,下意识往前追了两步,但在看到薛怀玉充耳不闻跑开的背影后,又停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