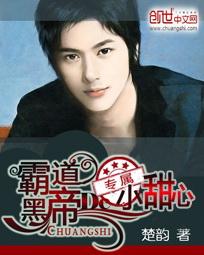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下嫁俗夫重生免费 > 第3页(第1页)
第3页(第1页)
可是,偏偏那女子不一样。
他宠着她,捧着她,纵容着她的一切,时光荏苒,盛宠依旧不见厌倦。
后院的女人们发了疯一般的开始妒忌,连她也不例外。
于是,也不知曾几何时,她变成了自己最厌恶,憎恨的丑陋模样。
她像个十足的妒妇,容颜逝去,悲春伤秋,无一所长;只能在后院跟着那些女人兴风作浪,想着如何能将那个被他手心的女人狠狠碾压,踩在脚下!
可笑的是这个世道,女子一旦嫁了人,便只能仰着夫家鼻息,恁凭再如何委屈哭闹,也显得丑陋不堪,不可理喻。
仿佛每日每夜都在折磨中,她看着新人倚在她丈夫怀里,那如花的笑颜,灿烂得太过刺目。
她又忍不住对比自己渐老的容颜,寂寞的庭院,合着那些小妾偏房的撺掇,在他出府办事的一个夜晚,安了个七出淫妒之罪,悄悄把那胡女绞死在屋梁上。
两天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闻迅赶回来,掘地三尺,抱着那胡女已寒的尸骨,提起了手里的刀,破开了她的卧房。
她着一袭盛装相迎,端庄娴雅,静坐在床榻上;她默默的看着自己名义上的夫郎,陌生得仿佛从不相识。
在这后院惶恐不安了十年,那一夜,却是她从未有过的平静。
萧宠本想替胡女报仇,一刀杀了她。
但他又何其的残忍?竟是一眼瞧出了她心中所想,收了刀,让侍从拿了笔墨,递了她一纸休书。
她不肯画押,他如地狱罗煞,切下她的拇指,这才在休书上画了押,遂把她赶出了候府。
她握着残指,在候门前嘶嚎,狼狈不堪,体面尽失。
想她少年时光,也曾天真浪漫,容华若桃李;被多少人捧在手心,却也不屑回眸一顾。
与今昔作比,皆是一场虚妄,一声叹息,一个笑话。
她用一枚发簪,换了一叶扁舟,还兑了一壶酒,江舟自流而去。
……
此时茉茉激动的扯了扯她的衣袖,将她飘远的思绪生生扯了回来。
“二姐儿,萧候长得可真俊!饶是这些眼睛长头顶的高门贵女都盯得发直了。”
梅二姐下意识偏头看向那矜贵年轻的萧候,不巧那萧候也朝她这边瞥了眼。
似是不经意间,眸光彼此偏擦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