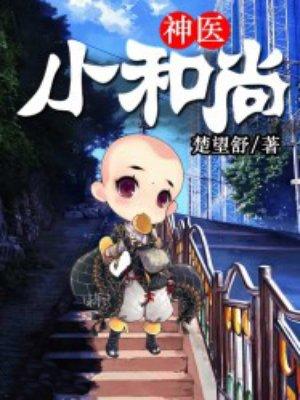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恰逢雨连天女主喜欢过柳朝明吗 > 第220页(第1页)
第220页(第1页)
朱南羡淡淡道:“哦,立后有什么规矩么?”罗松堂道:“回陛下,大婚的规矩繁多,立后倒是没什么,只需宣旨即可。只是,依照礼制,这道旨意该由先帝或先后来拟,然先帝先后仙逝,顺位而下,只有陛下您亲自来拟立后的圣旨了。”栀子堂外一时无人作声。过了一会儿,朱南羡道:“好,你八月初十传戚绫进宫接旨。”罗松堂讶然道:“陛下这是应了?”朱南羡不置可否。罗松堂又看了眼在立在一旁不言不语的沈奚与柳朝明,迟疑着又道:“陛下既应了,那初十廷议过后,臣便请柳大人,沈大人,还有其余各部堂官,后宫的两位太妃一并来奉天殿,等候陛下宣旨?”朱南羡默立了片刻,“嗯”了一声,随即绕开他,大步往未央宫外而去,抛下一句:“还有中书舍人舒桓。”白露节后,沈奚彻底解决了西北军资军费的问题,朝政虽仍繁重,好在没那么吃紧了。至八月,凉州卫传来消息,说朱荀与茅作峰二人分率先行军,最迟八月末可抵凉州城,而后行军卫最迟也会在九月中到。这一消息无疑让朱南羡与众臣大松了一口气,西北气候酷烈,若行军太慢,拖到冬月,无疑会给军资与驻防都造成负担。而提前半月抵达,也给兵将们争取了足够的休整时间。西北出征,这一朝中最为棘手的要务暂得以解决,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便是登基大典与立后了。八月初十当日,廷议过后,凡三品以上朝臣都未离开。守在奉天殿外的内侍吴敞唱过三声后,则见奉天殿门左右一开,戚绫一身海棠色大袖背子,臂绕云纹霞披,云鬓边的金步摇不繁不简,称得整个人温婉如芙蓉,又俏丽如春桃。她缓步走到殿中,拜下道:“臣女戚绫,参见陛下。”朱南羡道:“平身。”随即将手里的圣旨递给立在一旁的舒桓。舒桓展开圣旨,一抹愣色自他眸中一闪而逝,宣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定侯府四女戚绫柔嘉表度,德仪备至,笃生勋阀,克奉芳型,特赐封为贤礼郡主,自即日起,行郡主之仪,钦此。”众臣原以为今日等候的事册立皇后的圣旨,谁知朱南羡一道旨意反赐了戚绫郡主之衔。既为郡主,那便入了皇室宗亲,如此是再不可能为后为妃了。戚绫跪地俯身接旨:“郡主贤礼,戚绫,谢陛下恩典。”她的神情是分外平静的,仿佛早就料到了结果。朱南羡看着她,沉默了一下,说道:“戚绫,你与朕共患过难,也曾于危难之际帮过朕,朕一直记在心里,愿佑你一世福泽,但,加封立衔需一级一级地来,朕今日之所以在奉天殿宣读此旨,除了赐你郡主之衔外,还要当着众卿之面,许你一诺——待你大婚之日,朕会收你为义妹,册封你为我大随朝的公主,以公主之礼,将你风光大嫁。”戚绫垂眸跪在奉天殿里。说来可笑,她进殿的时候,其实在心里数过,除了已故的太后,她该是一七三章三声喝问出口,满朝文武同时撩袍跪拜而下。“秦桑。”朱南羡道,“取朕的‘崔嵬’来。”立在殿旁的侍卫随即呈上一柄通体墨黑,镶着鎏金暗纹的刀。朱南羡将“崔嵬”握在手里,缓步走到罗松堂面前:“景元二十三年,朕去南昌就藩,父皇念及朕对母后的思念之心,准允朕为她守孝两年不娶,而今父皇驾崩,朕——亦愿为父皇守孝两年,罗尚书,不知朕的孝心,你可愿成全?”罗松堂哪里敢应这话,瑟瑟缩缩地跪在朱南羡跟前,不住地磕头。朱南羡的目光在他身前册立皇后的宝册上掠过,忽然拔刀出鞘。刀光如水,擦着罗松堂额稍一寸处纵劈而下,宝册即刻裂为两半。朱南羡淡淡道:“罗尚书,这本宝册太旧了,朕给你两年时间,做一份新的。”语罢,再不多言,任凭殿中群臣跪了满地,负手阔步迈出了奉天殿。因新帝继位后还有一次官员任免,登基大典在即,八月的秋选反倒成了小打小闹,三品以上的大员全无变动。八月的最后一夜,星斗满天。隔日就是登基大典,因国丧而缟素了近两月的宫禁褪去一片白,露出原来的朱色宫墙,悲默的气息一下被冲散,取而代之的是乾坤轮转后,更加明亮,也更加沉敛的浩荡龙威。各宫上下都在为新帝登极的一刻奔忙着,宫人与朝臣彻夜不眠,满目匆匆色里充满了希冀与敬畏。就连被晋安帝勒令任何人不能叨扰的未央宫,也在这非凡的夜里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中夜子时,宫女余葵服侍苏晋吃完一道药,难以成眠,步至栀子堂外。堂外廊檐下,被朱南羡分来统管未央宫事务的内侍马昭正坐在檐下,仰头望向这漫天星斗。余葵看他这副十分专注的样子,格外好奇,问道:“马公公这是在瞧什么?”“余宫人还未歇下呢?”听到声响,马昭回过头来。余葵笑了一下:“怎么睡得着?等着栒衣去取新的革带回来,待天一亮,就该换新的了。”革带,即腰带。依大随仪制,每朝皇帝在位期间,宫人都需用绣有当朝年号的革带。同理,大臣们朝服的玉带上,也需镂刻上“晋安”二字。(注1)“马公公在看星子?”余葵顺着马昭的目光望去。“杂家听说,每逢新帝登基,前一夜的星斗预示着他的帝运。”马昭道,“闲着无事,所以随便看看。”余葵惊讶道:“马公公还会辨认星相?”如今能在栀子堂伺候的,无不是宫里最沉稳的人。这位马公公不过而立之年,身长七尺,面貌堂堂,听说是会些武,因此才被朱南羡派来未央宫,未曾想竟会观星。须知景元帝立朝后,为防宦祸,曾下严令“内臣不得干政,犯者斩”,后宫的内侍,多的是无学识之辈,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像马昭这样的,可谓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