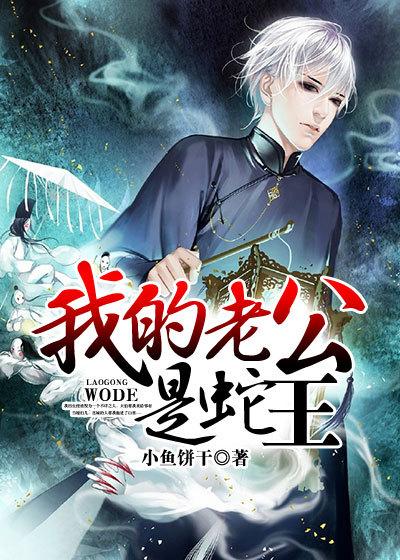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攻下那个小太监番外 > 第38页(第1页)
第38页(第1页)
心跳如蝴蝶振翅般,一下接着一下,规律地鼓动着胸腔。夏蝉在头顶声嘶力竭,却不敌她的心跳这般激烈。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情绪来势汹汹,顷刻间,便将她溺得喘不过气来。许是陆生有什么苦衷亦未可知……思绪混沌间,丝丝温热混杂着些微疼痛,从手腕处传来,唤醒了她的三分清明。姜离放弃了挣扎,脚步微转,与陆生面对面而立。陆生的目光牢牢地锁住面前的宫女,他听见自己不甘心道:“可以不走么?”说罢,垂于身侧的左手微微蜷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奴才岂有抗旨的勇气,更何况……窥见姜离眼中的决绝,陆生终是垂下眼睫,唇角溢出一丝苦笑。囿于皇城本就不是她的本愿,岂能因他一句话就放弃如此得之不易的出宫机会?是他痴人说梦了。只是这消息来得太过突然,他还未做好心理准备。况且,也不该在这般情形下道别。偏偏将他伪装好的皮囊剥开,叫她撞见了阴暗可怖的一面。他还有什么资格挽留姜离。她是即将飞出高墙的燕雀,而他,不过是皇城中随处可见的脚下泥罢了。他倏地松开了手,低眉垂目,敛住眼底汹涌的情绪,轻声道:“抱歉,弄疼你了。”姜离低下头,瞥向自己的手腕,只见上面缠着三两道拇指粗的红痕。陆生当真是使足了力气。她兀自摩挲着手腕,扯过衣袖,将其遮住,方抬眼看向陆生:“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年轻的内侍闷闷应了声,似乎又怕自己的态度太过消极,他牵起唇角,勉强笑道:“好。”心口好似有一张无形的大手覆于其上,缓缓收紧,闷得不像话。他本该说些体己的话,送上些美好的祝愿,让姜离安心出宫才是。可此刻的他却觉得开口是如此的困难。是以,眼睁睁地看着姜离冲他点点头,转过身,他方后知后觉地生出无力之感。小宫女步履匆匆地去奔赴她的锦绣前程,并未像从前那般冲他挥手作别。直至那道身影消失在道路尽头,她都未曾回头看他一眼。陆生垂下眼睫,掩住眼底的黯淡。终究……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陆生回到值房,只见程川并未离去,正坐在桌前静静地瞧着他。“你还在这做什么?”他已精疲力尽,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应付旁人。“还能做什么?”程川笑得满是恶意,“自然是留下来看你的笑话。”他自顾自地提起桌上的茶壶,倒了一杯水,往远处推了推:“陆监生,想不到你也会有软肋。”陆生掀开眼皮,冷冷出声:“你若是继续胡说八道,我不介意送你下去陪着胡管事。”“诶哟喂,我好怕啊。”程川佯装受了惊吓,捂着胸口往后躲去,眼底的恶意更甚,“你被那小宫女瞧见了真面目,闹崩了,不装啦?”陆生嗤笑道:“若你所言不假,亲眼目睹了胡管事落水,那你可看清楚了,是他欲害我在先,我不过是在求自保,失手将他推下。”是,他虽对胡炳坤百般嫌恶,却不耻主动对他动手,更不会愚蠢到用如此低级的手段害人性命。程川好似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将桌子拍得“砰砰”作响,直震得桌面上的茶盏移了位置。见他这般疯癫的模样,陆生眉头微蹙,眼底闪过一丝厌恶:“这便是你躲在水井后装神弄鬼的目的?为了看我的笑话?”“哈哈哈哈……”程川捧腹大笑,“陆监生,失手也是经你之手,你亲手害死胡炳坤可做不得假,如今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他竖起两根手指,在陆生眼前挥了挥:“一,跪下来求我替你守住秘密,将每月的俸银奉上,便可安稳地继续做你的监生。二么,若你不愿,那也好说,我会如实上禀梁总管,还胡管事一个真相大白。”说罢,他收起手指,撑住身下的榫条凳,晃动着上半身,冲陆生堆出满脸笑意。他可得睁大眼睛好好瞧着陆生这小子是如何向他跪地求饶的。空气静了一瞬。片刻后,陆生冷冰冰的声音倏然响起:“你当东缉事厂的人都是摆设么?”猖狂惯了的程川陡然变了脸色。他缓缓皱起眉头,眼中闪过困惑,只当陆生在虚张声势:“你不过一介八品内监,怎么会和东厂有勾连?”陆生懒得再与他纠缠,对此不置可否:“我确无甚大的通天本事,却问心无愧,你若想告发便去吧,左右我也不会拦你。”见他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程川不由得慌了神。“你……你等着。”说罢,他站起身,脚步凌乱地出了屋子。看着他踉跄的背影,陆生垂于身侧的手缓缓收紧。程川此人,亦留不得。-姜离努力攒着一股劲,愈走愈快,愈走愈远,直到精疲力竭,才停下脚步,弯着腰,大口地喘息着。待风滚过额头,将汗水拂去。她方直起身,抬头看天。今日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她的前路亦是一片光明。可她……为何却开心不起来呢?-[贰:飞出高墙]天刚蒙蒙亮,姜离便收拾好包袱,从耳房走出来。昨夜她躺在通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几乎熬了个通宵,此刻却不觉困倦,反倒精神得很。院里已围聚了十余名宫人,待阮箬昭在雪竹的搀扶下走出那扇黄花梨木门,便齐刷刷地跪了一地。“阮嫔娘娘安。”众人齐呼道。阮箬昭向前行了一步,抬手道:“都快请起罢。”众人依言站起身,恭敬地站在原地。他们在长春宫当值的时日并不算长,也偶有动过另寻高就的歪念头,可眼下,这位温顺的主子就要离宫,是以,都表现出难得的忠心来。时间紧迫,阮箬昭只象征性地说了些场面话,便遣散了众人。剩下的,便是几位关系亲密的宫人在依依不舍。月娥揽过姜离,又依次拉起雪竹和闵兰的手,面露忧色:“山高路远,路上怕是十分辛苦,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姜离鼻子一酸,点头应道:“都说了几百次了,我记得的。”“剩你一人在宫里我还真是不放心。”雪竹搡了把月娥,打趣道:“不若与我们同行,马车大得很,多塞你一个应当不成问题。”月娥哭笑不得,向后躲了半步:“你就别拿我逗趣了。”几人又说了些体己的话,一只厚厚的包裹忽然从斜旁插过来,落入姜离怀中。李嬷嬷的声音响起:“小丫头,这是嬷嬷自己做的糕点,嬷嬷也无甚旁的好东西,只有这做糕点的手艺还拿得出手,你们几个小丫头平日里吃惯了我做的菜,此行路迢迢,路上若是想这一口了,便拿出来吃些。”说罢,李嬷嬷抬起手,在几人头上挨个揉过。都还是半大的姑娘,路上也没个嬷嬷照顾,可如何是好。思及此,两行热泪自眼中滚出,姜离忙走上前,拿袖子去替她擦泪。几个小姑娘也围上前去,抱着哭了一会儿。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阮嫔娘娘,马车已在宫门前候着了。”有马夫前来催促道。闻言,几人虽不舍,却还是擦去眼泪,拿起行囊,依依惜别。最后望了一眼长春宫,姜离与雪竹、闵兰,阮嫔娘娘四人踏出院门,往外走去。车轮滚滚,惊起一地尘埃。姜离将头伸出马车窗外,回头看向城门。天色将明,这座巨大的城池落在此处,像一只将才苏醒的野兽,缓缓睁开朦胧的双眼,与她遥相对望。姜离胸口起伏,吐出一口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