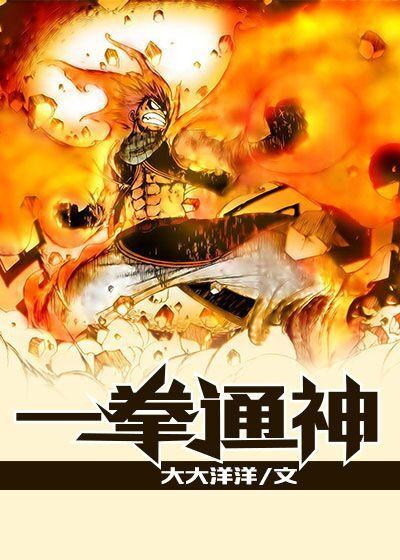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万箭倾心撒空空免费阅读 > 第64章(第2页)
第64章(第2页)
万惜忽然垂下头,咬|住了宁恒的耳垂。
她不要吻,吻太平淡,她胸臆中的情感异常强烈,吻已经无法表达。
她就是想要咬他,想要将他全部吞下,藏起来,不让人看见。
宁恒只能是她一个人的宁恒。
被咬得疼了,他“嘶”地吸了口冷气。
宁恒照旧躺在她腿上,偏转头,仰着,蹙眉看着她。
这个角度,令他喉结更为显现,像是山峦,像是刀锋,像是一切危险的,不可碰触的。
可她偏偏要碰。
她再次垂首,咬住他的喉结。
这次,对他而言,不是疼,是忍耐。
开关被打开,再也无法关闭,他一跃而起。
在万惜还没反应过来时,宁恒忽然将她打横抱起,朝着二楼房间走去。
他上楼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她耳畔都有风声。
“别这么快!”她尖叫,并用力搂着他的颈脖。
幸好最后,她的背脊没有摔在坚|硬楼梯上,而是躺在柔软被单上。
“宁恒,你是要……要……”她努力撑起身子。
“你。”他却将她压制住。
要你。
窗外有无数的烟花在盛放着,除夕的夜,值得所有的快乐。
他吻|着她,那个吻,不似昨夜,是志在必得,带有进|攻性。
她被吻得迷迷糊糊的,好不容易才抓到半分清明,趁着换气的间隙问道。
“等下,不是说,不是今天吗?”
她记得宁恒在客厅里说的话——“放心,不是今天。”
房间里没有开灯,但烟花的光,间歇盛放,亮如白昼。
他的衣服,落在了地板上。
“没错啊。”他笑,低低的笑声,敲击着她的心脏。
她视线所及,每一根肌|理线条,都是明晰而利落。
“已经过了十二点,是隔天了。”他说。
他收拾好自己,又来收拾她的衣服。
她的衣服,也落在了地板上。
简直是强词夺理。可她能怎么办?
窗外,仍旧是漫天的烟花,不断地爆|破着,升腾着。因为只有瞬间的璀璨,短暂的盛放,因此那光有凄艳的穿透力,落在了墙上。
墙上,有树影,也有人影。
都是交织缠|绕。
如果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星球,他的手,则在她这颗星球上迷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