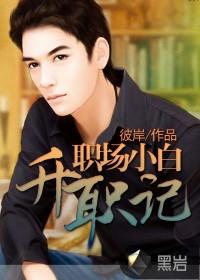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重生后追妻火葬场txt > 第58页(第1页)
第58页(第1页)
本就这一条命罢,为故人豁了去,实在值得。--------------------分道扬镳“天下万般事,哪能都有姑娘说的那般巧合?”詹文通向后退了几步,开口的声音也变得嘶哑,他忽而觉得自己应当是真的老了,老到他已经记不清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都是如何度过的,老到那些滔天的仇恨似乎也随着时间被一一抹平了。似乎如若不是今日云烟瑾诘问出口,便是再也没人提起这些事情来,它们便要腐朽地跟他一同埋进土里,如同他那些永不见天日的故人一般,再没有人记得真相本来的样子。“爹……”詹罗如不知何时已从言晏的身后站了出来,她在詹文通将要倒下去之前,先上前一步扶住了他微颤的身子,那个一直挡在她身前,为她遮风挡雨的父亲,似乎只是在此刻,突然就倒下了。“我一直等着有人问起我这件事情,我等了许久,也过去了太久,久到我甚至以为自己也许等不到了,”詹文通退后两步,跌坐回了椅子上,好似山雨来时被摧折的苍树一般,似乎已经忘了这样守护了半生的真相其实从来不曾是个秘密,是因为人们惧怕,所以才让它深埋地底,“凌空派当年是何等的光景,武林中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而门主夫妇二人更是出了名的善人,他二人游历江湖那数十年更是不知搭救过多少条性命,散去多少钱财,可灭门至今,竟无一人,”詹文通猛地一拍桌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似是憋的太久了,全然不记得在他面前的众人也并非是昔日旧友,因为连他,也并非是旧日的模样,“竟无一人曾想过为他们报仇,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竟……竟无一人啊……”“宗主这叫什么话,那屠了凌空派满门的妖女已坠崖而死,你还希望他们来讨什么公道?”云烟瑾每说一次这样的话,便觉得是在自己心上捅了一刀,刀刀见骨,刀刀血红,仿佛以此便是偿还,便是赎罪,便是提醒自己不能忘记,不能湮灭那份仇恨,只要有人记得,有人追问,那便能有告慰九泉的一天。“呵…呵呵……,她一介小小女子,哪怕是武功盖世,又怎能屠尽满山之人,凌空派满门当年多少武学奇才,难道都能被一个还未长成的女娃娃取了性命。这般的弥天大谎,天下人居然信了,哈哈哈哈哈,咳咳,天下人,天下人可知是那——”詹文通猛地上前一步抓住了商陆的手,目眦欲裂地如同地狱之中爬出来的恶鬼,半分没有武林盟主的做派,他急切地想要从那双眼睛里看出些什么,哪怕是半分影子也好。鹤熙情急之下想要上前一步的动作被站在一旁,低头不语的云烟瑾给拦了下来,他这才发现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起,他竟也不自觉地将商陆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害怕他们受到伤害。“盟主为何不能,就让死去之人死去便罢了,何苦,何苦徒增事端。”商陆出声打断了他的下文,言辞恳切,似乎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他说死去之人便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还能如何,而活下来的人活着便够了。“你在说些什么!”云烟瑾抬头时已是一副通红的眼眶,泪水流不下来,反而徒增几分可怖,她不可置信地拽住了商陆的胳膊,说出口的话是她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声竭。“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原来…如此……”詹文通骤然松开了那双紧握的手,笑出的声音甚至不像是喉咙里发出来的。“只是公子并非旧人,若是不能体会其中仇恨之深,也实属情理之中。可人命并非草芥,公子既然是医者,想必应当明白这个道理。”詹文通再抬头时,眼中的最后一丝光亮终于落下,他转身之时,满身的生气似是迅速衰败,一副颓靡之势,颤颤巍巍地朝后院走去,是他糊涂了,从他当年犹豫的那一刻开始,一切便已都无法挽回了,他又怎能寄希望于等一个早已下落不明的人,终究是他老糊涂了。“对不住了,各位,我父亲他平日里并非如此的,许是今日,”詹罗如埋怨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商陆身上,可是,看起来那人似乎也并非是毫无触动的样子,甚至他为何看上去比父亲还要难过,那些话,便是真的出自他本心吗?人非草木,便真能做到如此无情吗?以及为何,詹罗如皱了皱眉,停顿了半晌,却还是觉得那些记忆似乎太过遥远了,为何连她也觉得眼前这人熟悉的很,他究竟是谁?来此究竟带有什么目的,还有身旁这个人,詹罗如不由地站的离言晏远了一些,这才继续说道,“还请各位就此下榻,我马上找人来给各位安排住处,如此,我便先失陪了。”“不会不会,是我们叨扰了才是。”鹤熙下意识地接上了一句,又忙不迭地上前了一步,这才发现人家小姑娘的眼神全粘在晏儿身上,半分都没有分给旁人。而这平日里呆头呆脑的小傻子的脸上,也是不由地出现了几分担忧的神色,只是两人这手抬了几回,终究是没有握到一处。直到那小姑娘转头跑了出去,那傻小子的目光才终于敢毫不遮掩地落到人家的背影上,情之一字,果然是不可说,鹤熙摇了摇头,转身看向另一侧,显然又是一片血雨腥风。“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让詹宗主继续说下去?”云烟瑾觉得自己已经逐渐看不透眼前这人的想法,或者说难道是她从一开始就看错了,还是,还是她从来就没有认清过。“你也看到了,詹宗主为此劳心劳神,我只是想劝他不要拘泥于过往罢了。毕竟往事沉积,总是心病,长此以往,五脏六腑无一安生,我只是站在医者的位置上,如此说法而已。”商陆背对着众人,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再无精神解释这些莫须有的编织的理由,有何遮掩的,漏洞百出的谎言。“倘若是你的亲人,你也能做到如此的不在意吗?别人的性命在神医您的眼里,就真的可以如此轻贱吗?那些枉死的人,他们不需要一个真相吗?”云烟瑾不知道她在质问谁,甚至不知道眼前站着的人究竟是谁,或者说她到底是在为了谁,求一个真相,求的究竟是什么真相。“就算求得真相又如何?我已说了,人死不能复生,执着于此难道就能让那些死去的人回来吗!你为何从来不懂,咳咳,为何不懂生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那么多人的死换来了一人的生,不值得好好珍惜吗!”商陆鲜有这样气愤的时刻,甚至连这般大声说话的时候也是少有,因而连着站在一旁的鹤熙和言晏都被他此举吓了一大跳。可是两人欲上前的步伐却是踌躇不已,到了最后,也还是任由那二人持续着这场无言的对峙,直到最后,云烟瑾背对着他们的身子终究是忍不住地后退了几步,这才出声打破了这诡异的沉默。“正是,在你眼里,苟且偷生也算生,死原本就是不值得的,在你心里是不是觉得人就要不择手段地生,毫无指望地生,哪怕父母亲人全都枉死也无关,只要能活便好,是吗?”这话连着晏儿这般不通事理的人也觉得云烟瑾这话说的太过分了些,只是事已至此,他们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劝下去,让这场闹剧收场。“是啊,正是啊,若非如此,你又怎会……,罢了,原本一切便都是我自认为的,你原本便不想来走这一遭的,是我强求,这才害的你平白耽误了许多日子。既是如此,从今往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道不同,再不相为谋。”腰上的长剑似乎冷的惊人,云烟瑾是用力握住了剑柄,这才不至于让自己倒的太过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