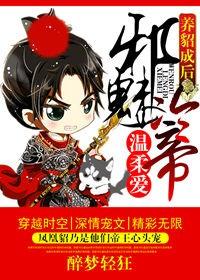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素女经原文及白话文 > 第194章(第1页)
第194章(第1页)
何念新背靠着墙,蹭到了怀夏的窗边,小心翼翼地敲了敲,而后闪开。
她静静等着,一会儿如果来人是服侍的下人的话她便另寻办法提点下怀夏自己来了,如果是怀夏自己开门的话,她就可以闪进去了。不曾想,她等了挺长一会儿的,竟都没有人来开门。
何念新有些奇怪,又蹭着墙摸到了窗边,戳破了窗户纸,想往里看看。
她正好瞧见了怀夏的卧榻,此时怀夏和千曲姐妹两人正互相倚靠着,只是坐在床头,却都闭着眼睛,竟是睡了过去。何念新哭笑不得,怀夏急忙忙地把自己这么叫过来,她倒是挺安心地睡了。
她心想怀夏房中应该没有别人了,便又摸到了门口处,自己把门推开一条缝隙,闪了进去。
然后何念新便差点惊叫出声。
只见正对着门的座椅上正坐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正一脸沉思,正是当今太后。
何念新像是做坏事被抓了个正着,立刻挺直了身板,正在想着是赶紧再开门跑掉,还是去里面抢了怀夏就跑。太后她是见过的,老太太又没有身负绝世轻功,肯定是追不上她的。
但开门声已然惊动了太后,太后微抬起眸子,蹙眉看着她:&ldo;你莫非是……安河?&rdo;
何念新:&ldo;……&rdo;她压低了声音,故意道是,&ldo;您认错人了,安河是谁我不知道。&rdo;
&ldo;同清平那丫头交好,又上蹿下跳像个猴儿,也便是安河你了。却不知你们这是使了什么手段,才改换了模样。&rdo;太后却道是,&ldo;外间如何了?&rdo;竟像是个普通的老妇同亲戚家的孩子话家常。
何念新一时语塞,半晌才道是:&ldo;二皇子已经没了,三皇子还好好的,侍卫们去救了。&rdo;她尽量撇清这里面自己的干系,绝口不提自己在其中掺和了什么,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太后的模样,自然仍旧是随时准备着冲去捞过怀夏就跑。
太后却是一滞,道是:&ldo;哀家并非是问这个,宫中之事,等下自会有人来回禀哀家。更何况,哀家已经下了令,等寻到了二皇子,带去到皇帝面前去,由皇帝处置。&rdo;
太后这么说着,声音低沉了下去,神色间带着些许怅惘无奈。兄弟阋墙,于皇家显得那般平常,太后似乎也是早便想得到,总有这么一天,是以她并没有震怒。但她却未曾料到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又会这么惨痛地让她一日之内失去了两个孙子,是以她仍旧怅然,不愿再多去管这件事了。
更何况,这兄弟间争的,是那天下最尊贵的位子,早便不是她这个深宫妇人能去管的了。
何念新倒是有些奇怪:&ldo;您不是问这个,那您问的是什么?&rdo;
&ldo;我是问,这宫墙之外,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了?&rdo;太后目色幽远,仿似透过窗户,望向了天外。何念新却是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个尊贵的妇人,这漫长的一生里,也未曾有过那么几日,能真正地看一眼宫墙之外。
太后对宫墙外的事只是茫然,却仍旧觉察出了山雨欲来的满楼狂风。而今这场混乱,也只像是一场前奏罢了。
何念新一时沉默。
太后却忽觉自己失言,竟失声笑道:&ldo;罢了,这哪里是哀家能过问的事。&rdo;这笑里全是苦涩。
天底下最尊贵的老妇人,却仍旧桎梏于牢笼。
何念新想了想道是:&ldo;我父王是冤枉的,是被圣上猜忌了。圣上猜忌的人有很多,他不能信任的人也很多,这次的事恐怕没法轻易了解了。&rdo;
太后没有回应,而是沉思着什么,倏尔又轻笑,这回像是陷入了回念,总算是真正有了笑意:&ldo;那时你父王还小,老贤王他们夫夫两个不会带孩子,时常便带着你父王入宫来,你那两个爷爷便各执一词,让哀家来评判一下,他们两个管教你父王的法子谁说的对。你父王是哀家看着长大的,他的心性如何,哀家是知道的。此次皇帝要发兵,哀家便劝了几句。但哀家毕竟是深宫妇人,不好多说,只能去庵里供奉香烛,求个平安。&rdo;也未曾说她究竟是求的谁人平安。
何念新不曾指出这点,只不住往怀夏那处看。怀夏向来是个警觉的,更何况外头出了这种大事,她有可能因太疲惫而小憩,但不会睡这么死。
太后自然是瞧出了她的担忧,道是:&ldo;是哀家下的令,教她们两个先好好睡了。&rdo;
何念新警觉了起来。睡觉这种事怎可能是下令就能睡死的,眼前的这老太太定是下了药!
&ldo;你不必担心,千曲撞见了不好的事噩梦连连,这样才能睡得安稳,清平不过是哀家叫人顺便为之罢了。&rdo;太后又道是。
何念新想了想,姑且放心下来。
&ldo;说起来,哀家倒是教你们这些小丫头狠狠摆了一道。那石碑什么的,是你们两个做的吧?&rdo;太后竟在这时算起了账,&ldo;哀家这也算反过来摆你们一道了,就此两清罢。&rdo;
何念新一时语塞,摸了摸鼻头,心里头道是这两清用得怪怪的,却不敢说出来。
&ldo;罢了罢了,以清平心性,想尽办法也要回宫,那必然是有要是要做。&rdo;太后似乎并不恼,只道是,&ldo;现如今细细想来,清平这孩子,打小就是个伶俐的。也不知你们私下里都做了多少事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