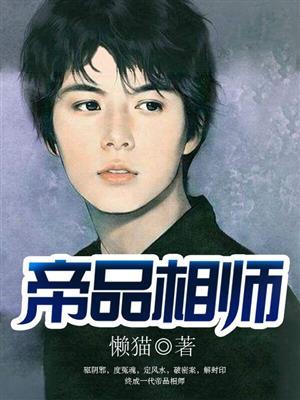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大脚娘子 凌玉 > 第18页(第1页)
第18页(第1页)
他对平芯红有信心。日积月累的歧见有其杀伤力,不是简单的示好便能修正。在这之中他可是下了不少工夫,对此有着极大自信。即使现在申叔华似乎已痛改前非,但是谁能保证他不会重蹈覆辙,又回归公子哥儿的本性。而他是绝对会在背后推他一把的。巧芸没有他的心眼多,不能明了何以他仍旧如此气定神闲,难道他不明白两人在申家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吗?过去申家没有个男人持家,所以将大部分希望寄托在吴天浩和两个孙子身上,即使对家宝的出身多所疑虑,却都没敢声张撕破脸;但是眼前申家正牌的传承香火者回家了,申家二老便有恃无恐,定会对家宝的身世加以调查,不会再对她们母子和颜悦色。“难道你不怕他们夫妻在这期间培养出感情,等到叔华想起谁才是加害他的真凶后,他们夫妻俩再来个沆瀣一气,那时你我还有机会吗?”巧芸一想到这景象,忍不住打了个颤,寒意直窜。吴天浩不是被吓大的,他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在申叔华与平芯红之间,因为当初让他们夫妻失和的条件仍然存在。“你不用穷紧张。”他捺着性子安抚巧芸。“难道你在万花楼里是混假的吗?你不会再拿出过去那套狐媚之术,在他们之间煽风点火,搞得他们鸡犬不宁,因为无法相信对方终至分裂吗?”他出言点化后,巧芸一改忧色,反倒是满脸跃跃欲试。狐媚手段她都快还给老鸨了,要是让窑子里的姐妹淘知道,搞不好会笑她越混越回去。这世上还有比看不见的感情还要不可靠的东西吗?感情自男人口中说出比纸还要薄,一戳即破;从女人口中说出还不是有所要求,要的是男人荷包里白花花的银子,若还附带了房子、珠宝那更好。人要有钱才有地位,才是个角色,外头那些人鞠躬哈腰看的不是人,而是趸放在金库里的、存在钱庄里的银子;口中说着阿谀谄媚的话,心里想的是能由对方身上刮出多少油水。要不这么想的那就是圣人了,这种人不是已经作古,就是还没出世。不必有天眼通神力,吴天浩也能明白,巧芸的心思已经转到如何分化申叔华和平芯红的计划上,有了这件事,便可以让她忙和一阵子不来烦他。他有自己的计谋,没时间应付她,也没那个心情。但是他并非没有意愿再和她翻云覆雨一番。为了对外保持君子风范,他得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多多留意,不能落人把柄来伤害得来不易的名声。而为了讨好平芯红,他不能猴急,得慢条斯理,一点一滴地松弛她的心防,好引她上钩。像她那种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和窑姐儿不同。受到礼教的束缚往往外冷内热,蕴藏在她体内的热情,需要男人谆谆善诱方能澎湃勃发;而他会是那个男人,他会让平芯红在他的教导之下,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鱼水之欢,而沉溺在其中。不过他不必像个苦行僧般虐待自己,虽不能对外发展,但是在申府内却有自己送上门来的。巧芸本就不是贞节烈妇,能在寡居生活中守得住;况且她在进申府之前就和他姘上了,既然如此,他们何不旧缘重续、各取所需?在申府只要隐瞒得当,不教仆役抓到把柄,没人敢对他怎么样。出了申家大门,他仍旧是那个正气凛然的表少爷,等着继承申家,完成他成为人上人的梦想。他猛一使力将巧芸带入怀里,埋首在她雪白的颈项间啃咬吸吮,留下点点红印,一双手不安分地解开她的衣襟,露出大片细嫩香滑的肌肤。“别胡来,家宝就在外头,万一让他瞧见,不小心露了口风,那咱们努力至今的成果岂不是付诸流水。”巧芸在他的怀里早已经茫然不知今夕何夕,但是想到了儿子倒教她恢复了一丝理智。她抓住他在身上探寻的手,阻止他再更进一步。“放心,他做我的儿子不是做假的,哪有老子精明小子笨拙之理。况且咱们的事也不是从今日开始,他老早就学乖了,知道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来吵我,否则我的教训不是好受的。”听到他的说法,巧芸不禁蹙紧眉,她不喜欢脑子里跃过的第一个想法。“你打儿子?你怎么打得下手,他还那么小,身子骨又不好,连碰一下我都不舍得了,何况是打!”她看起来大有跟他拼命的态势。“儿子是让你给惯坏的,现在若不好好管教,将来难成大器。”吴天浩气愤地说道。“要管也是申叔华才有资格管,你只是表叔,充其量也不过是教书先生,不要儿子儿子地叫。”巧芸厉声告诫他,眼忙着四下转着,生怕有第三人听到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