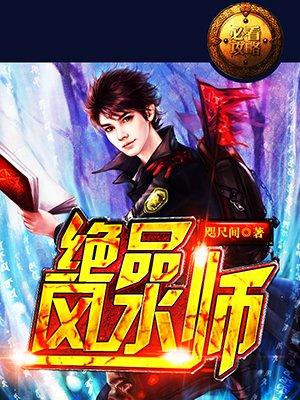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这金主有毒作者暮寒公子 > 第22页(第1页)
第22页(第1页)
死后不肯离去,依然在等着尚未赴约的意中人,这一等就等了两千年。不过他也再没法等来泾渭分明常思走后,白芷翻着从熟识的警官手中得来的近期失踪人口的资料,企图找到犼的下落,看了几眼之后叫苦不迭,被一堆密密麻麻的文档折磨得头都大了。白芷早在千年前就不喜欢看书念字,因为出身武将世家,老爹在他的学业上也并不怎么上心。倒是有一个人,生得一张俊脸却总是皱着眉头,比教书的太傅还古板,喊着他的字絮絮不止:“重山(chong),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是要多看些书才好。”要不就是:“诸葛先生曾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每每这个时候,白芷不胜其烦,总会哼着轻浮的曲子,戏弄他:“我看你比书中的颜如玉还好看,不如多让我看两眼?”当时,长身玉立的少年白净的脸上眉头皱得更甚,一身月白长袍的衬托下更显得脸上红晕诱人。年少的时光总是无忧而短暂,后来,他登基为君,月白长袍换成了黄袍;纨绔子弟白芷则一夜间宛若脱胎换骨,继承父业,做了护国杀敌的将军。两人之间行的是君臣之礼,讲得是客套官腔,除此之外再无旁的交集。再后来,有人献谗言,白将军功高盖主,长此以往恐民心不稳。好一个功高盖主,还真是看得起他。自始至终,他白芷想护的就只有那个人的江山,他想要的也只是那个人而已。然而,薄凉最是帝王家,白芷的兵权终究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被一分为三,将军令形同虚设。白芷赋闲在家,心想,那个人的书可真没白读,罢免兵权都能说得像是真心实意为人着想一般。再再后来,敌国突然来犯,直捣国都,朝廷重臣竟有一个是外贼奸细,兵权一时难以调集。年轻的帝王只能率众仓皇出逃,敌军在后围追堵截,白芷率亲信死守最后一道城防,想着自己多撑一刻钟,那个人就能多一分生的机会。流矢破空而来刺入身体的时候,白芷咬了咬呀,不在意地抹去越流越多的血迹,直到眼前变得模糊,白芷用剑支撑以半跪的姿势望着那人离去的方向才阖上了眼睛,弥留之际想着自己还有话没同他讲,还有话没有问清楚。因着这份难以纾解的执念,白芷死后在破败的城门前辗转来回,草枯了,树绿了,雪落了,起风了,日复一日,却没等来他的君王。失地被收复,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是一张熟悉的老脸,白芷想,自己家的老头子总算还是有点用处的,只是不过一年光景,原本身体健朗的老爹却像老了十几岁。白芷遥遥冲着队伍行进的方向跪拜,狠狠磕了几个头。而白芷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等的那个人在出逃的路上莫名害了一场大病,早早的就已经去了。穿梭在人群中没有人能看得到他,相等的那个人也再无法相见。到了这境地,白芷反而不知道该去哪里了。索性就随着早就存在的一股吸力,任由它把自己带去了冥界。见到端坐在高位上的人,白芷意识到,原来鬼还是有心跳的啊,不然怎么会在看到寂尘的脸时,觉察到自己的心跳漏了几下。狂喜过后便是无尽黯然,眼前这个人虽然又换回了月白衫,可再也不是尚未登基之前的那个人了。在人间须臾二十几年,不过是历届冥主的一场考验,堪破情爱者、舍离七情六欲,才能成为冥主。白芷虽然心知肚明,知道有些话已经不用问了,但人总有一种劣根,又或者说是一种韧性,一种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到头破血流不肯回头的偏执。白芷还是忍不住问他:“你二十余年未曾立后纳妃,是不是因为也把我放在了心上?”寂尘:“是。政泽确实是因为你。”乍一听隔得有些久远的名字白芷还有些不适应,却忘了少年相伴时唤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名字了。政泽,年轻君主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