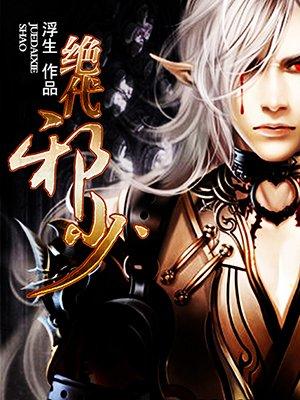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琉璃钟琥珀浓容九免费阅读 > 第167章(第1页)
第167章(第1页)
车子开了约莫大半个钟头,连马路上的车声都听不见了。
她听到“咿呀”一声重门开启的声音,猜到车子大概是开进了某个宅邸,怪就怪在又行驶了一段路,七拐八弯的竟都不见停,又觉哪里不对。
等到货车停下,车门打开,有人上来将藤筐搬下车,云知将脸埋在蜷起的膝盖上,一口气高高吊到了嗓子眼上。
好在那些人只负责搬,货落地之后便不管了,等车重新驶离而去,周围恢复一片寂静时,云知扒开一个缝往外探去。
是一间屋子……很大很大,简直像是一个仓库,抬头可见之处是云顶檀木做梁,哪个仓库会长这副模样?
她环顾一圈,确定周围没人,这才掀开筐盖,跨身而出,一股腥味扑鼻而来。但见这偌大的屋子除了这些菜筐之外,其他货箱传出“咕咕咕”的声音,她凑近一看,有鸡有鹅,还有一个长条大桌,上边摆满了各种鱼肉食材。
这里莫不是什么酒楼的后厨?
她飞快踱到门边,耳朵贴着门面听了听,好像是没动静,于是深吸一口气,手指叩着虚掩的门,缓缓推出,身子一点一点前倾。
直到看清了门外景象,她才直起身子,迈出门外时简直生出一种脚踩棉花上的飘忽感。
一派恢弘印入眼帘,四望茫茫,红墙白雪,雕栏玉砌应犹在。
五格格彻底傻眼。
这里是紫禁城。
第六十七章小小朝廷“……”之前是……
显而易见,这间堆满鸡鸭鱼肉菜的屋子还真是间“仓库”——专供大内御膳房所用食材的南库。
长廊自东往西,有数间这样的库房,只是负责清点厨役们还没点到这里,才给云知拣了个空。
她的大脑大约空白了那么几秒,听到隔壁库房的人声,方醒过神,眼疾手快先跨出走廊栏杆,矮着身,顺着小道钻入园中。
这可真是白日奇谭了!她怎么就到皇宫里来了呢?
她回忆起那声腔,莫非在市集,那个同沈府府兵叫板的人是内务府的采办?
正困“惑”着,忽从不远处传来一声长长的“传膳——”,正是典型的小太监声音,从养心门方向一声声传递到这儿,不等回音消失,便见几十名套着白袖头的太监们抬着摆满食具瓷罐的长桌,浩浩“荡”“荡”地往明殿方向而去。
云知蹲在一面影壁后,约莫等了七八分钟,才等这一长长的行列走出西长街。
她又不禁生产生新的疑问:大清都亡了,这养心殿的御膳怎么还似从前那般阵仗?
尽管,皇宫对她而言曾算“半个家”,但现如今的紫禁城是个什么状况,她知悉不甚。报纸上能说的,无非是民国“政府”建立之后,给了些清室优待条件,大致上就是同意小皇帝溥仪和太妃们继续住在宫中,只是如何个“优待”法,宫墙外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莫名进了宫,要说心不慌是不可能的,但比起被沈一隅逮回去,眼下的情况又似乎好了那么一丁点。只要等到那辆货车再来,想办法混上去自然就能再回市集,不就能顺利出宫了?
如此,反倒不宜离开御膳房太远了。
最好能找一处相对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
她思来想去,记起离这最近的有个佛堂,既无僧人也无太监,除非特殊节日,大多时都是门庭紧锁的,或是个适宜她藏身的好去处。
这么想着,一面留神着墙外的人迹,一面动身。
皇帝用膳,大多管事太监都候在养心殿外,她另辟蹊径,潜往佛堂,这一路竟十分顺当,没撞见什么人。
佛堂门前悬着乾隆御题的“智珠心印”匾额,上了锁,里头没人。
雪愈发大了,她抱着略微单薄的肩,跺着小碎步给自己增添热气。也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绕行一圈,意外发现一扇窗没关全,捡漏似的翻过窗,总算得一瓦遮头,喜出望外。
光看佛像和供物上的灰,应有一阵没人来打扫过了。虽说暂时脱险,可这么冷的天,她要挨饿受冻一整天下来只怕够呛。
于是翻翻找找,从案条边寻到一盒火柴,将殿堂前的烛台点燃,手心凑过去补补热气。
不知怎么的,忽然就想起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起先自己把自己逗笑,听外边一阵风声呼啸的,寂了寂,她忍不住想:说不定我真的会冻死在这儿,没冻死,被宫里的人发现了,一样要遭殃。
她下意识去看时间,一抬手腕,这块墨蓝“色”的表面瞬间将她带回换表的那个夜晚,想起他许诺她的“三十一号”之约,委屈之意涌上心头,鼻子不受控制的发酸。
明明这么这么努力的逃出来了,怎么还是见不到人呢?
她一个人委屈巴巴的哭了一会儿,不晓得是因为那零星火光发挥了一点作用,还是临近正午,熬出了日头,身上总算恢复了暖意。女孩子一旦舒坦,心绪就跟翻书似的转得快,她一下子又从悲观主义转换成了乐观主义,掐指一算,再熬六个小时天就黑了,皇帝晚膳通常不会太迟,库房那儿天一黑一般没什么人,到时回去应该稳妥。
云知对着佛塔,虔诚的磕了几个头,心里默默许愿平安出宫。
只是不等天黑,忽闻门外锁头被开的声音,有人进来了。
她原本跪坐在蒲垫上,整个人被冻的有些昏昏欲睡,听到声响时要躲都来不及了,一回头,却是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站在门边,用同样大惊失“色”的望过来:“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