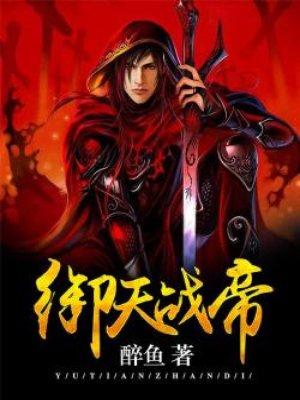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什么七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那寨主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一茬,他一时间觉得孟小安说得话似有古怪,但是又说不清楚到底怪在了哪里,嚅嗫着应了。
而后才反应过来,分明先前的“左护法”已经说好了让他们加入魔教,怎么现在又变了卦?
秦凤娇看到了那寨主怀疑的眼神,连忙赔笑道:“叫寨主见笑了……其实是这样的,左护法诸事繁忙,便叫小女来联系各位,小女又怕各位寨主看不上只好谎称自己是魔教的左护法,这事儿让教主知道了,大发雷霆了一通,而后便叫小女来解释清楚,实在是小女自作主张,还望各位大侠莫怪。”
那寨主一愣,脑子里便转了好几圈,而后觉得,说秦凤娇自作主张是假,派她先来试探一二才是真,毕竟以魔教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这几个山寨根本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倒也没有什么好图谋的,一会儿为自己表了衷心而庆幸,一会儿又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所烦恼,那寨主半天也没接上话来。
孟小安一看便知道事情是成了。
原本按他的意思,这些山寨就放着不管算了,毕竟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许多都是被秦凤娇几人哄骗着当了山贼的,实际上在山下村庄里都还有田地,也饿不死自己。但后来又想,反正也是要赶路,不如溜达一圈全都收归门下。
这些人对魔教来说好比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能用他们反将一军倒也不错,宋一金既然是宋家的人,那么这次的行动便是宋家针对张思勉所设计的,如今宋一金已死,但秦凤娇还活着,虽然宋家对秦凤娇肯定不如对宋一金放心。
但总聊胜于无。
又安抚了几个山头,将那些人都招到了魔教麾下,孟小安这才放下了半颗心,又留了管宁儿和大半的魔教弟子下来,让管宁儿盯着秦凤娇和这里的几个山头,在事情完全被他掌控之前,变数总是越少越好的。
原本事情也就这样有惊无险的过去了,却在临走时突然听熊五爷抱怨道:“可惜了不能真的劫持了皇子给朝廷找麻烦,实在是朝廷欺人太甚!我上山前村子里又有好几个被鬼蚕剥了皮的人,可报到了县令那儿,县令却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还说那是一种传染病,要把我们这些去问的人全部赶走,好在爷爷在山上还有个宅子,不然这么多人如何安置!”
孟小安对于“剥皮”这两个字尤为敏感,几乎立刻问道:“什么?”
熊五爷又道:“咱们村子里先前有许多人被鬼蚕附了身,死的时候形状可怖,整张脸几乎都会被毁去,鬼蚕会从人的嘴里爬出来,我也曾经见过几次,那情景实在是骇人至极……村中的人去找县令和知州,偏偏县令和知州都装聋作哑,只当做无事发生,这两年来被鬼蚕附身的人越来越多,上头下令说是传染病,整个村子都被封了起来,我们几个正好上山打猎,逃过一劫——之前想要回去,又被人追杀,这才无奈成了山贼。”
孟小安和孟小宁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来了点震惊。
蛊虫是南疆特产,而王蛊又极难炼制,即便是魔教多年追查,也才知道了蔡重光和路既白这两人而已,但以熊五爷的话来说,他们村子里被喂了王蛊的人似乎不仅仅只是一两个,至少也应该有十数个之多。
“你可知道最开始染上鬼蚕的都是些什么人?”孟小安皱着眉头看着熊五爷。
熊五爷道:“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也有些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我小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说那些人是活该,说是他们以前做了很多有损阴德的事情,所以才会遭到报复。”
“有损阴德?”孟小宁似乎想到了什么,但他并没有说出口:“比如?”
熊五爷压低了声音,极小声的说道:“盗墓。”
孟小宁的表情一变,张思勉也意识到了这也许是事情的关键,但以蔡重光和路既白的身份来看,他们是绝不可能与盗墓扯上什么的关系,其中一定还有另一条线,把这些人全部串联起来。
其实光听熊五爷的描述是不够的,虽然仅从描述上看,熊五爷说的那些人与蔡重光和路既白的死法几乎一模一样,鬼蚕和王蛊应该也是一个东西,可是到底不能直接看到,也不能完全确定下来——只是那个村子里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活人了,死掉的人县令一把火把尸体都烧光了,而活着的人能逃出去的大多都逃了出去,没有逃的也是知道自己的身上已经有了鬼蚕,就算是逃也没有什么用了。
“我听村子里的老人说,大概是三十多年前,来了一队人马,看样子就知道肯定是大地方来的,我们这种小村子从来也没有见过那样气宇不凡的人,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进了村就说我们村子的风水极好,是个宝地,这种地方下面一定有着很多好东西,当时村子里的老人们就说他们不是要干好事,但他们有很多的钱,村子里还是有十一二个人听了他们的蛊惑,跟着他们进了山。”
“进山约莫大半个月,才从山里回来,进去了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回来了七个,里头还疯了两个,剩余的五个人也都性情大变,一旦有人提起那天的事情便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十年的时间里这几个人陆续都去世了,死状都一样凄惨,大家一开始都以为是诅咒,直到有人正好看到了那人死去时从他嘴里爬出来的鬼蚕,这才知道他们是被不好的东西寄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