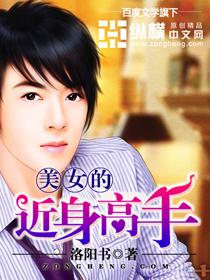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宝珠鬼话番外人面桃花 > 第62页(第1页)
第62页(第1页)
可是我根本动不了。眼睛可以清楚地看轻房间每个地方,我甚至还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三奶奶打呼噜的声音,可我就是没办法让自己稍微动那么一下。半晌感到脖子边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对着我一下一下吹着冷气,我转着眼珠子想朝边上看,可是什么都看不到。我心绷紧了。想出声叫,但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尝试着想扭一下头颈,刚一用力,耳朵里轰的一响,好象整口江在耳朵里倒翻了,我只觉得一边太阳穴昏天黑地一阵尖锐的疼。那疼让我身体条件反射地一抽,只那么一下,身上那种被什么东西给压着的感觉消失了,我嘴一张,一声尖叫:“林绢!!林绢!!!”“啪!”灯亮,刺得我眼睛一阵生疼。闭上眼下意识钻进被窝,片刻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我奔了过来,坐到我床上,手伸进被窝把被脚朝边上掀开:“怎么啦宝珠??”噼里啪啦机关炮一样的话音,是林绢。我睁开眼,眼睛依旧是刺痒的,被灯光照得有点睁不全,可是脸被她抓着,所以只能勉强抬起头,迎着光线朝她看了一眼:“绢,我……”“啊!”没等我说完,她对着我一声尖叫:“你的眼睛怎么啦?!!”“我的眼睛……”被她这种样子吓了一跳,我刚被灯光稳定下来的心脏又开始乱跳起来,挣扎了一下把身子撑起,冷不防碰到手的伤口,痛得我一咧嘴:“哇!”“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正捧着手抽气,门再次被推开,林绢她三奶奶睁着双惺忪的睡眼站在门边上对着我俩看。片刻目光停在我脸上,她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几步走到我身边,捧住我的脸:“怎么回事,你碰过啥不干净东西了闺女?”我被她们先后的表情弄得僵住了。隐隐觉得有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在我脸上发生了,我看了看三奶奶,再看看林绢,用力睁了睁我那双不知怎的异样厚重的眼睛:“绢,拿镜子给我。”“别看了,你先躺着。”一边把我往床上压,一边看向三奶奶:“快把叔叔他们叫来,快啊!”“哎!哎!”应着,匆匆忙忙朝外头走去,我看着三奶奶的背影突然有种很不祥的感觉:“绢!把镜子拿给我!”“别看了别看了,就是有点肿而已。”拍着我的肩膀,她好声安慰我。而她这种样子让我更不安了,一把推开她的手,趁她还没反应过来,我一骨碌爬起身直奔向梳妆台那面大镜子,对着镜子里的人仔细一照,这一看差点没把我的魂给吓了去。镜子里那是张什么样的脸啊!肿得跟只猪头似的,两边的脸颊都透明了,从太阳穴到腮帮子,朝外微鼓着在灯光下隐隐发光,像镀了层釉似的。而更可怕的是我那双眼睛。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感染了,上下眼皮红得像肉冻,朝外鼓胀着,把本来还不算小的两只眼睛挤成了一条线。怪不得刚才怎么睁都觉得睁不开来,都肿成这样了,还能睁得开吗……牙关节一阵发抖,对着镜子里这张异形似的脸。“绢……”话还没出来,眼泪先下来了,我脚一软一下子坐倒在地上:“怎么会这样……”当晚我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因为林绢扶我上床时发觉我身上很烫,量下来一看体温超过39度,所以等她叔叔婶婶一到,几个人二话不说把我架上了车。进医院后我整个人就开始觉得不行了,之前在家里没有感觉到的症状,不知道是因为吹了夜风还是一路上的颠簸,一进医院闻到那股浓烈的消毒药水味,一下子就发作了起来。只觉得浑身疼,每根骨头都重得像要从身上垂下来似的,虽然身上裹了两条毛毯,人还是一个劲地发抖。林绢吓坏了,一路上用我的手机尝试着和狐狸联系,可是电话打过去始终没有人接。不知道狐狸和铘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这种时候我也根本就没心思去管这些。只一味恐慌在我身上的变化里了,明显感觉到进医院后自己的脸比刚睡醒时又肿了不少,特别是两只眼睛,痒得恨不得用手去挖。而身上又酸又冷,虽然平躺在医院的床上,可是难受得整个人躺不直。血样报告出来后医生给我挂了几瓶点滴在病床边吊着,他说我发烧是因为伤口发炎了,而脸上的肿是因为青霉素过敏。林绢当时就反驳那个医生,说我们之前来医院看时伤口处理得好好的,而且还打了抗炎药,怎么还会发炎。医生对此解释,虽然用了抗炎药,但并不能保证伤口百分百就不会被感染,也许是因为之后又接触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引起的。林绢又追问青霉素的问题,她说这是医疗事故。但医生矢口否认青霉素是他们这里打的。事实也证明医生没有撒谎,因为把之前的病历卡和打针单子拿出来翻了个遍,确实没有给我开过青霉素这帖针剂。于是我们只有沉默。当然沉默不代表就能接受这个事实。总也想不通,即使后来这一系列事情过去之后,每每和林绢谈起,我们始终是想不通,既然不是在这个医院里打的针,而我除了这里又没去其它任何地方就疹,那让我过敏成这副样子的青霉素,我到底是从哪里给沾染上的。吊完点滴后,天已经亮了。几瓶药下去似乎没有立即发生什么疗效,烧依旧保持在39度以上没有退,脸还是肿得让我感到太阳穴发疼。两只眼睛倒是不痒了,不过也已经肿得差不多已经睁不开了,我猜之所以不痒,肯定不是药起作用了,而是它们根本就胀到了极限。医生让我留院观察,我没答应。我想回家,回城里的大医院彻彻底底做个检查,因为我始终对青霉素的事情感到可疑,并且耿耿于怀。林绢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虽然叔叔婶婶的意思是让我留在医院,她还是坚持着把我带回了三奶奶家。其实坐在后车厢一路颠回去的时候,一度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车颠得我难受得想用什么东西把自己的骨头砸碎。想起从林绢家到我们住的城市那段不算短的路程,我不由得担心我是不是能够扛得住。万一中途又发生什么病变怎么办,至少在医院,还是随时能得到必要的治疗的。但是想到回去后可以得到的彻底的治疗,我还是决定忍。半顿饭的工夫总算进了村。这会儿天色还早,很多人都还没起床。蒙着层晨雾的田埂上只依稀一两道身影在那边慢慢晃动,远远几只野狗听见了引擎的声音,一路追了出来,又在摸不找的地方跟着车甩着尾巴汪汪叫。再转个弯,就能看到林家大院了。大院正门锁着,新漆的门上两个光鲜的“喜”字,门下满满当当一层红艳艳的碎片花似的铺了一地,是昨天晚上放完了之后留着装点个喜气的鞭炮。车子转个向驶向大院的边门,林绢的婶婶把裹得像只粽子似的我从车座上扶了起来。“来,宝珠,沾沾喜气。”经过那片碎红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一边发着抖一边循着她指的方向对着那片热闹的颜色看。正准备听她的话沾染点喜气,冷不防眼角边什么东西一闪,把我困难地缩在肿胀眼皮子下的视线给转了过去。下意识朝那东西闪过的方向看了一眼,就看到刚才车子开过的方向,那道大门边上不远处一棵槐树下头,一个人站在底下盯着我看。白色的衬衣,白色的裤子,在被雨水冲成了黑色的树干边看上去突兀得有点刺眼。意识到我的目光,他又看了我一眼,而我随即认出这张脸,是昨天连续碰到过三次的那个不知道是新人哪一方亲戚的男孩。“看什么呢?”正对着那方向继续看着,车停,林绢拉开车门拍了我一下。我回过头由着她和她婶婶把我扶出车。站稳脚步等着她去泊车的时候我又朝那棵槐树下看了一眼,那男孩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黑漆漆一根弯曲的老树映着身后一片被雾气弥漫的田埂,不知怎的,看着身上冷不丁一阵阴恻恻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