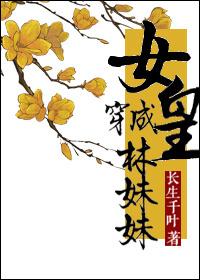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灵魂出窍介绍 > 第21页(第1页)
第21页(第1页)
他忽然发狂般地想念起应许来。他掏出手机,挣扎了半天,终于调出了应许的电话号码,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了一句话:你现在身体还好吗?注意休息,别抽烟。发完以后,他盯着手机等了很久,手机却毫无反应。他苦笑了一声,以前应许给他发短信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回复。他放下手机,翻箱倒柜地开始找和应许有关的东西,琢磨着用这个做借口去酒店里见她一面。床头柜的容嘉心理诊所在s市滨江区的一条街上,前后各临近商业副中心和s大,它的门面并不起眼,韩千重找到它还颇费了点周折。他找到的那份病历卡是应许的,上面只是记录了她就诊日期和配的药,没有其他信息。每周基本固定一到两次,每次配的是几片艾司唑仑片——上次他在大法山别墅看到的那瓶安眠药。应许的身体向来很健康,怎么会定期去医院看病?揣着这个疑问,韩千重走进了这家病历卡上的心理诊所。前台是个甜美的护士,看了看他的病历卡,疑惑地看着他:“是的,这是我们诊所的,请问你想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韩千重沉声说。护士被他的表情唬了一下,让他稍等,飞快地跑到里面去了。没过一会儿,有个医生走了出来,约莫三十几岁,目光锐利地落在他脸上:“请问你哪位?有什么理由要求调看病人病历?”韩千重愣了一下:“我认识她。”“不好意思,所有病人的资料在我们这里都是保密的,除非你有搜查令,我们可以配合调查。”医生淡淡地拒绝。“那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你们为什么要给她配安眠药?”韩千重十分生气,“你们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吗?”医生愣了一下,敏感地问:“出了什么事了吗?她已经很久没来诊所了,而且,从七月开始,我就没有再帮她配过安眠药,如果你质疑我的问诊,你可以去医疗署投诉我。”韩千重语塞,好半天又问:“那麻烦你告诉我她得的是什么病?”医生的口风很紧:“对不起,我不方便透漏,这是病人的隐私。”韩千重重新打量起这件诊所来,诊所的墙上贴着两名医生的照片,眼前这位医生是第二个,姓秦,叫秦丰,国心理学硕士,各种名头后面排了一大串。心理学……心理诊所……一股浓浓的不安从心底浮起,韩千重刚想放下面子恳求,那秦医生已经往病房里走了,顺口对前天护士说:“麻烦他出去吧,我正在治疗,别让他骚扰了其他病人。”韩千重想要追上去,几个护士拦住了他,他只好冲着秦医生急急地叫:“我真的是她很亲密的人,我只是担心她……”秦医生的脚步顿住了,他回过头来,眉头微皱:“请问你叫什么?”“我姓韩,叫韩千重。”半个小时后,韩千重坐在了秦医生的诊室里。诊室里布置得温馨整洁,一进去就有种亲切的感觉。靠窗的位置是面对面的两张布艺沙发,餐桌、躺椅都设计成了家居的形式。“这两年来,我听到过无数遍你的名字,”秦丰盯着他,慢悠悠地开了口,“一直在脑子里勾勒你的形象,今天见面,和我脑子里的差不多。”“应许说的?”韩千重觉得有点气闷,他从来不知道,应许居然已经看了两年的心理疾病。“是的,”秦丰陷入了回忆,“她非常矛盾,从她的叙述里,可以看出你对她无情冷漠到了极点,可是,她还反复地帮你辩解,还妄图从我这里得到佐证。”韩千重的双唇紧抿,挣扎了半天才问:“她到底是什么病?”秦丰沉默不语,良久,他才轻叹了一声说:“我和你的谈话,有悖于我的职业准则,可我不说,却又违背我的良心道德。”“请你告诉我,”韩千重恳求,“我对她没有恶意。”“抑郁症,从两年前的中度,到两个月前的重度,我一度想要联系她的家人,可她坚持不肯,到了后来,她甚至不来了,连手机都打不通,说实话,我非常担心,因为她有很严重的自杀倾向。”秦丰迎视着他的目光。韩千重的手脚冰凉,深深的恐惧从内心深处泛起,重度抑郁症……那个美丽聪慧的女子,驾驭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女子,他朝夕相处的枕边人,居然会得了重度抑郁症?他居然连半点都不知道!“我对你挺好奇的,”秦丰略带深思地看了他一眼,“我一度以为你是应许杜撰出来的,因为很多病人有臆想症,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念头。一个漂亮、富有的女人,对你有恩,更对你一往情深,你却居然能这样冷落了她六年,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韩千重苦涩地笑了,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说应许很爱他,爱得发了狂,就连这个心理医生都这么说。以前他越听到这话越愤怒,为什么应许爱他,他就非得也回爱她?而且,他压根儿不觉得应许爱他。她只是把他当成了宠物,宠到了没边,或者只是想要占有他,他越是难以驯服,就越是能让她费尽心思。“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她……其实……并不爱我。”他有点困难地挤出了一句话。“不爱你?”秦丰的表情十分惊愕,“你居然觉得她不爱你?她做的那些事,连我这个旁观者听了都动容,你居然觉得她不爱你?”“我……”韩千重茫然了,应许爱他吗?“其实,自从到我这里就诊以来,她的抑郁症曾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中间她的病情反复过两次,每次都和你有关。”秦丰皱着眉头,眼神中带着深深的谴责。“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说她和你曾经一起参加了一个酒店的情人节活动,种了一盆花,对吗?”韩千重的脑子有片刻的空白,旋即,剧烈的疼痛从心底泛起,心脏好像被一刀刀戳成了筛子,又被放了盐腌渍了一样,他究竟做了什么?“一盆石莲花,你一朵,她一朵,据说,因为石莲又名宝石花,花语是永不凋零的爱,所以这个活动叫种爱对不对?”韩千重木然点了点头,那盆花被应许放在了阳台上,每天都哼着小曲去瞧一眼,搬来搬去的,晒多了怕晒死,淋到了怕涝死,那花被她拾掇得挺水灵的。可后来那盆花蔫了,叶子很快就一片片发黑脱落,到了最后成了一盆干瘪瘪黑乎乎的花干。开始发蔫的时候,应许还每天蹲在阳台上琢磨着怎么救它,买了好多书,甚至请了一个花木师来。最后彻底死绝的时候,应许坐在阳台上喝了一晚上的酒。他头一次感到了心虚,因为,他看着那盆花烦,倒了一杯满满的隔夜水在上面。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也不知道那个花盆被丢到哪里去了。秦丰回忆着:“那是她最严重的一次发作,她原本就有失眠的症状,那会儿就更厉害了,每天后脑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躺在床上会有窒息、心悸的感觉。”“后来我花了很多精力疏导,她的自我调节能力挺强的,有段时间她在我面前表现得甚至挺开朗的,还对我说,她想明白了,她要放你自由,她答应过自己,给自己六年的时间,如果不能让你爱上她,她就放弃。”“我有点大意了,因为我曾经有两个治愈的病例,治愈的契机就是病人表现出对执念的放弃。可七八月份的时候,她的病情一下子突变了,从她的叙述里我听得出来,她非常矛盾,也非常绝望,整晚都无法入眠,我要求她和家人一起过来一趟,因为她的厌世倾向十分明显。可她告诉我,她家里出了点事情,她父母扔下她走了,是真的吗?可能就是这个压垮了她,”秦丰轻叹了一声,吐出四个字来,“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