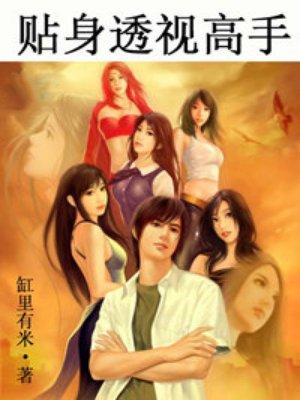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红豆生民国好看吗虐吗 > 第125页(第1页)
第125页(第1页)
这与老幼妍媸无关,舅舅舅妈骨子里毕竟老派,总归是没影子的事。“那你还想东想西的。”贺云钦看看她莹白的侧脸,用手中的笔点了点桌上的另一沓资料,一本正经道,“既然不想睡,那我们就来补补德语。”自从红豆跟学校请假,他就顺理成章接过教导功课的任务,只要有空,每晚都会强行拉着红豆学功课,补完顾筠带来的笔记还不够,还以德语的学习不能中断为由,强教红豆德语。她想也不想就摇头:“不要不要,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动脑筋。”她的脑袋靠在他颈窝里,摇头的时候,柔软的发丝一下一下擦过他的脸侧。“真懒。”他看出妻子有了困意,声调放低,“要不我们重新再定几个名字。”“不是早就定好了么。”她抬眼瞄瞄他,“一个叫‘光明’,一个就叫‘真理’。”他摸摸下巴:“会不会太随意了。”她闭上眼睛,让自己更放松地窝在他怀里:“贺光明’、‘贺真理’,朗朗上口,叫出来也大气。我觉得挺好的。‘”可万一都是女儿呢,‘贺真理’也就算了,‘贺光明’老觉得不够秀谧。红豆知道他又在琢磨了,真是够了,九个月了还没定下来。她想起脚踏车上刻着的那句‘lightandtruth’,懒懒道:“别纠结名字了,你先告诉我,你们当初怎么想起来用旧脚踏车来做联络方式的。”贺云钦没想到她突然想起来问这个:“我加入组织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分给我的那辆还格外的旧。”原来是这样。红豆愣了一会,不满道:“可不是太旧了!第一回坐你车,居然还刮破了我的裤子。”他怔了怔,低笑道:“还记恨这件事呢?”她嘟起嘴:“一辈子都记得。”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举动,她都记得。他望着她,眼里笑意加深。其实他也记得,当时在富华巷里因为此事两人第一次起争执,过了这么久,她气鼓鼓的样子仿佛还在眼前。想到这,他莫名有些恍惚,忍不住抬手去轻抚她的脸颊,不知不觉间,岁月化作流动的金沙,静悄悄从指间淌走了。他即将为人父,而他的红豆,马上要做母亲了。“红豆,过几天余管事要带人整理庭院,我让他们在院子里种一株红豆好不好。”她鼻息渐渐变得匀缓,许久才含含糊糊嗯了一声,显然困极了。他低下头,极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睡吧。”她这么坐着睡不舒服,他小心翼翼抱着她起身,打算把她送到床上去。谁知刚一动,红豆嘶了一声,皱眉摸向肚子。他的心立刻提了起来:“怎么了。”红豆静静感受了一会,既期待又紧张,抬眼看向他:“我可能是发动了。”贺云钦后背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默了默,强自镇定:“好,别怕,有我在。”话这么说,毕竟最担心的事终于来了,接下来该如何安排,他脑中竟半点头绪都无,好几分钟过去,只顾抱着红豆在屋中打转。红豆都快被他转晕了,以往何曾见贺云钦如此失态过,不由哭笑不得:“贺云钦,你冷静一点,先放我到床上,再去通知安娜大夫。”贺云钦这才回过神,镇定地将她放到床上,打开门唤下人备车,又让人速给安娜大夫打电话,一转眼的工夫,贺家上下便鼎沸起来。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对贺云钦而言,简直像一百年那么长,再轻微的动静,只要是从产房发出的,都会令他心惊肉跳,无奈产房条件有限,且因同时有两名产妇待产,只能由女性长辈陪产。他在走廊枯等,活像被扔到油锅里煎熬,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五脏六腑都快熬成了渣,等到下午,当他几乎到了忍耐的边缘时,产房终于开了门。他的心仿佛被重重捏了一把,高高提在胸膛里,双脚则像陷入泥淖中,一步都迈不动。岳母笑得合不拢嘴:“母子平安!大的是哥哥,先出来三分钟,晚出来的是妹妹。”耳边炸开众人的欢呼声,他胸口停滞了的血液,重新咕噜噜奔流起来,顾不上看岳母怀里的孩子,分开人群,疾步朝产房走去。三天后,红豆母子平安出院。贺太太和虞太太忙着安置一大两小,贺竹筠赖在二哥二嫂房里,贺孟枚为了多陪一对宝贝乖孙,干脆搁下一干杂务留在家中,一整日,贺公馆笼罩在欢悦的氛围中。红豆产后体力未恢复,孩子们晚上要喝奶,依着贺太太和虞太太的意思,未出月子前,贺云钦不宜跟红豆母子共住一室。该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贺云钦的强烈反对:“妻子生产,丈夫不好好陪伴,为了清净反倒躲开,说来简直荒唐,这等陋俗早该易除了。”说这话时他站在窗边观摩下人换尿片,回绝得理直气壮,红豆撑着胳膊看躺在身边的真理,听了这话心里自是甜蜜。贺太太和虞太太讶笑对视一眼,红豆生产受了罪,在医院时,贺云钦眼睛一刻都不舍得离开红豆,几天下来,人都熬瘦了一圈,她们早该料到贺云钦不肯另居一室。好在卧房里外都收拾整洁了,贺家新旧观念共存,在听取安娜大夫洋派观点的同时,亦不肯摒弃根深蒂固的老观念。譬如是否开窗,虞太太和贺太太因为担心红豆吹风,无论如何不同意开窗,贺云钦则怕屋内空气污浊,反倒不利于红豆的恢复,坚持要开窗。两派观点互不相容,贺云钦求同存异,少不得拿出好口才与两位母亲周旋,最后勉强达成了里屋关窗、外屋开窗的共识。接下来又磨合了好几处,忙乱了好一晌,才将一大两小都安置好了。期间,好些亲友打电话,因为分隔两地,隔着战火,无法亲自来探视,只能以这种方式前来道喜。等一切都安顿好了,几位长辈笑眯眯地坐在外屋,轮流将小真理和小光明抱在怀中稀罕,才出生,兄妹俩不是酣睡就是吃奶,可是孩子们的每一个呵欠、每一次无意识的睁眼,都会引来长辈们欢天喜地的议论。直到孩子们睡了,他们意识到红豆也需休息,这才依依不舍地散了。贺云钦抱着小真理进里屋找红豆,女儿前一秒还安安静静在他怀里睡觉,转间就啼哭起来,他无措了一会,先看女儿的尿片,没湿,于是抱着女儿进去,很笃定道:“应该是要喝奶了。”奶妈汪嫂跟在后头,二少爷俨然有经验的模样,她看在眼里,忍不住笑道:“是要喝奶了,二少爷,把小小姐交给我吧。”红豆在床上伸出胳膊,笑着接话道:“先给我看看。”贺家早备好了两位奶妈,但根据安娜大夫的建议,红豆应尽量亲自哺乳,一来更有利于孩子们的营养,二来能促进红豆产后恢复。贺云钦将安娜大夫说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只要红豆醒着,尽量先让红豆亲自哺育两个孩子,可惜红豆仍然掌握不好哺乳的正确姿势,奶量也少得可怜。贺云钦小心翼翼将女儿放到妻子的胳膊弯里,顺势靠着床头躺下来,看妻子撩起衣摆,低声道:“有奶么?”本是认真的语气,不知为何,说出来又让人发窘,奶奶红着脸一笑,忙轻手轻脚退了下去。红豆瞟他一眼,贺云钦自己也大不好意思,笑了笑,沉稳地自辩道:“我是怕真理没轻没重咬你,到时候你又该嚷疼了。”“说得我多娇气似的。”红豆咕哝,“那是我不会喂,今天早上我喂的那一回不就很好,母亲说了,往后会越来越熟练的。”说话功夫已经溢出几滴淡黄的乳汁,红豆如获至宝:“你瞧!”忙凑近哺给嗷嗷待哺的小真理,贺云钦紧张地注目着妻子和女儿的一举一动,小真理不但顺利地吮到了奶|头,裹奶时腮帮子还一鼓一鼓的,看来妻子总算掌握了些技巧,不必担心她又被咬疼,这才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