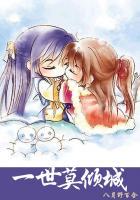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昭昭天明笔趣阁 > 第33页(第1页)
第33页(第1页)
程彻和那几名轿夫却没有出现在?堂上,但即便如此,堂下已经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看得县令和师爷都一个头两个大,不知?该从何人问起。“沈忘!”县令已经没了那日的好脾气?,沈解元也不叫了,直呼其名道:“我问你,何故深夜击鼓鸣冤!”沈忘拱手一礼:“回大人,沈无?忧此是?为纪春山师徒鸣冤,靖江县尸魃之祸另有隐情,还望大人明察!”“沈忘,本官上次就已然对你言明,此案已了,真凶已死,你怎地还苦苦纠缠!本官念你一时技痒,又有功名在?身,是?以并未对你乱动尸身,惊扰死者一事再行?惩处,你若再执迷不悟,莫怪本官大刑伺候,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县令被人扰了春梦,本就气?不打一处来,再见沈忘为了寒云道人的案子跟他没完没了,当下火气?顿起,也不在?乎沈忘还有在?京城做官的兄长?,只想疾言厉色地先把此事弹压下去,再行?计较。这一听大刑伺候,趴伏在?地的春山先哆嗦了起来,师父当日惨死的面容浮现在?眼前,他登时泪流满面地叩头道:“请青天大老爷息怒,莫要?怪罪于沈大哥,一切事由皆由小?的而起,不关沈大哥的事!”“大人!”沈忘再次拱手而拜,其声清越,不卑不亢:“既有诽谤之木,便有敢谏之鼓。太祖年间,尚有龙阳县青文胜为百姓击鼓鸣冤,吊死于登闻鼓下,为民请命流传至今。而今圣上英明,民殷国富,正是?尧舜之时,又岂能因噎废食,不闻急案冤屈?”“若真是?天日昭昭,判案公道,大人又何妨一听!”那县令生得肥头大耳,这夜里突遭变故,脸上的油腻尚未洗净,此时被沈忘一激,登时急赤白脸,如同一只油光可鉴的肥蟹。他正欲开骂,却闻听身旁的师爷轻声咳嗽了一声,低声嘱咐道:“大人,这沈解元名声在?外,据说京里贵人也对他青眼有加,还是?听他说说,再行?判断。”县令只得将满腔的怒火咽了回去,闷闷道:“本官也不是?独断专行?之人,你既说有冤屈,那便细细说来。只是?有一点,若你敢自负功名加身,信口?开河,本官也自有办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沈忘面无?惧色,甚至还露出了隐约的笑意:“大人断案如神,待听完学生的分?析,自有定断。”他走到常氏师徒身边,长?袖一摆:“学生所言真凶,便是?跪于堂下的常氏师徒,常新望与常友德。”一听提到自己的名字,二人蠕动着身躯开始嗷嗷不休,却原来他们嘴中被程彻塞了布团,有口?难言,只能流着涎水呜呜乱叫。县令面露厌恶之色,怒道:“休得喧嚷!待沈解元说完,你们再行?申辩!”沈忘垂头看着二人,眸中燃着隐约的怒火:“这还要?从三年前的大疫讲起……”嘉靖末年,大疫,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而在?这千人共哭,万户同悲的时日,一对儿来自湘西的师徒却决定北上,做点儿死人生意。然而,一路行?来,这对儿师徒花光了资财,却终无?所得,不得不滞留在?靖江县,做起了扎草人的买卖,挣点儿散碎银子糊口?。而同一时间,一位豆蔻少女?也随着流民的队伍来到了靖江县,卖身于一位富户家中,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婢女?。他们原本毫无?瓜葛,然而命运的手笔如此刁钻,让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串联在?一起。“常新望,常友德,在?得知?了为商会起梁的十位青年人一夕暴毙之时,你们心中便已经有了计较。你们发现,祖传的手艺在?这时竟有了用武之地,你们曾经最?忌惮的身份,此时却成?了你们最?为得意的倚仗。”“苍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它自作主张将春山师徒送到了靖江,也送上了绝路。寒云道人不学无?术,好贪小?财,是?以装模作样开坛做法,孰料,却正中了你们的下怀。你们趁夜,从义庄偷运走十具尸体,自己留下一具,再将剩下的九具放置在?位于茶山之上的白荡河上游。”“砍断沿河的树木,制作简易的堤坝,让尸体暂时滞留在?河床上。同时,模仿道家阵法,在?上游的石穴中故布迷阵,以将罪责推到寒云道人的头上。那日,正是?缠绵欲雨之时,待得凌晨果降大雨,堤坝冲毁,九具尸体顺流而下,引得沿河众人惊慌万分?,而你们也恰恰身在?人群之中,为自己创造了绝妙的不在?场之证。”“大人且看”,沈忘从袖中掏出一物,呈与县令,县令两指轻捻,一会儿拿近,一会儿拿远,疑惑地看向?沈忘。“这是?我在?白荡河上游河床中的一段雷击木中寻得的,这个布团乃是?各色麻线虬结而成?,正是?九具尸体所穿的麻布衣被雷击木上凸起的木茬所勾连,大人可命仵作将布团中的麻线,与九具尸体所穿的衣服一一对照,即可得证。”县令一听,那布团乃是?尸身所穿丧服所成?,厌恶已极,远远丢在?案桌上,急道:“何不早说!晦气?!”而这时,常新望已将口?中乱塞一起的布团吐出,嘶声大喊道:“大人!休要?听这沈忘胡言乱语,大人案子早有论断,这沈忘欺世盗名,妄想借此案立威,大人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尸魃之祸(十八)闻听此言,县令本就隐晦不明的面色,愈发难看起来。他如何不知?,沈忘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春山师徒翻案,无异于?当众给?了他一记脆亮的耳光,而他碍于?公理颜面,又只能坦然受之。堂堂县令,竟然要被一小小解元玩弄于股掌之中,岂不荒唐!为?今之计,他只有咬死所断之结果,无论?如何也不可向沈忘低头服软。这样一来,明明处于对立面的县令和常氏师徒,此时却?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齐心合力地蹦跳着,想要逃脱沈忘的围捕。“沈忘,区区一布团又能说明得了什么?这……这不是随处可得的东西吗!你难道就想凭此物翻案?”县令厉声喝问道。沈忘抬眼看着他,却?是悠悠地笑了:“仅凭布团,自?是不可能翻案。因为?活人尚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却?欺死人有口不能言,有冤无处诉。但是大人,天日昭昭,法网恢恢,即便是死人,也有辩白的可能。”他拱手一礼:“还请大人命衙役仵作将此案相关尸身呈上,学生自?会找出?让凶手无可辩驳的证据。”沈忘那略带轻蔑的凉涔涔的笑意激怒了县令,但是沈忘的要求在情在理,他又无从辩驳,只得不耐烦道:“既然沈解元都发话?了,还不把尸首呈上来!”很?快,本就有些拥挤的堂上愈显逼仄,当是时,众人或跪或站,众尸身并排而躺,冲天的血腥与腐臭味儿顶得坐在堂上的大老爷都一个趔趄。可怜那漪竹姑娘,已?是怕极了,也忘记隐藏自?己与尹焕臣的恋情,拼命往尹焕臣身旁瑟缩,引得上官宝珠频频侧目。别?说是普通人,就连验尸无数的老仵作也是面色泛白,略显慌乱。唯有沈忘,容色不改,甚至愈发平静沉着。他将盖着尸体的白布一一掀开,将那惨死的众生态呈现于?诸人面前。他每掀起一块白布,众人便跟着惊呼一声,掀到最后,漪竹姑娘已?然闭起眼睛,任由眼泪顺着苍白的脸颊流淌下来,让人见之生怜。沈忘没有在意众人的反应,只是目光炯炯地盯着堂上的县令。靖江县令可不能像漪竹姑娘那样,眼不见为?净,他强迫自?己保持着尚算端正的仪态,强压下涌上喉头的酸水。见县令尚能保持镇静,沈忘便蹲下身,指着许老爷深可见骨的伤口道:“大人请看,这处创口极深极重,正是造成许老爷死亡的致命伤。而此创口隐约可见的白骨之上,有一处被锐器磨损的骨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