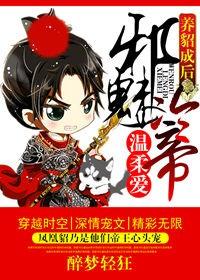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你的荣耀我的狙35章 > 第44章(第2页)
第44章(第2页)
“澜哥,疼得厉害吗?”
郁江澜这才发现有人进来了,蜷着的身子一点点打开,然后若无其事地坐直,微微笑下,“没,我只是活动一下。”
“活动一下?”凌季北神色陡然变了,语气不善,“那你起来。”
郁江澜微诧,他还是第一次从看见凌季北这么正经,那黑白分明的瞳眸,此时紧紧盯着自己,又一字一顿地说一遍:
“那你起来呀。”
郁江澜暂时还起不来。
这样拉扯脊柱来放松腰肌的方式,虽然可以有效地缓解腰疼,但是每次做完大腿根都会麻上半天。
他没做声,手试探地在身侧撑了撑,果然没起来。
也许是源于身体的力不从心,郁江澜忽然有些恼,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偏偏要在自己的病上较真,于是冷冷回应:“你吃饱了撑的?”
看着他这副“遗世独立”到不需要任何人靠近和关心的样子,凌季北有些无奈:“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这么喜欢逞强啊?”
“我也不明白了,你就这么喜欢让人难堪?”
“我这是关心你!”
“用不着。”
凌季北被他这三个字狠狠一噎,唇角抽搐,“哎你这人?你昨晚还说…”
他话说到一半停下了,有点晃神,反应过来那番话是醉酒后的郁江澜说的,他大概已经不记得了。
郁江澜却是忽然紧张起来:“我说什么了?”
你说,已经好久没吃过别人剥的鸡蛋了。
你说,谢谢你凌季北,谢谢你,对我好。
你说,你想有个家。
…
不知不觉,凌季北的眉眼间已经镀上了一层柔光。
昨夜星辰缠绵,两人紧密相拥时的温存一直到此刻还未散尽,郁江澜难得袒露的脆弱,就像一颗温暖的种子,根深蒂固地埋在他的心底。
所谓酒后吐真言,那番真言,所幸听到过,也就足够了。
凌季北认真了两秒,随即换了副没正形的模样,出其不意地朝着郁江澜后腰伸手:“你说你腰疼,要我给你揉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