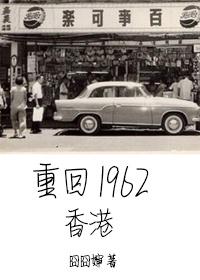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此夜星辰非昨夜下一句 > 第31页(第1页)
第31页(第1页)
难道,还在广场上?是了,以前就是这样,若她没言语,他就不举动。一时间,她被自责压得喘不过气来,慌慌张张就往大殿前去。弟子房就在大殿之后,绕过去不过片刻。是夜,月光皓洁,整个广场如被霜雪覆盖,皑皑生辉。然而,这偌大广场之上,却是空无一人。冉悦只觉自己的心也被这霜雪掩埋,冷得颤栗。前因后果,诸多伤痛,让她不自禁地想到一个地方——宿星潭。……宿星潭,现世与彼世交汇之地。已死之灵,若对现世存有执念,便会被灵羁吸引,于潭中现身,化为“战灵”。而同样的,灵羁消散,战灵便会回到宿星潭。若有他日再有相合的灵羁,亦可再次召唤。倘若战灵自己毁去灵羁,后果则完全不同。灵羁缔结之日,一切便由主人掌控。凭战灵自身之力,却无可能切断灵羁。若执意断绝,唯有身入宿星潭,借取潭中的彼世之力方可成功,但战灵自身亦会在这力量之下灰飞烟灭。灵宿宫立派以来,从未有战灵自毁灵羁。其一,是因战灵皆对现世存有执念,又岂会自寻毁灭。其二,战灵平日皆收在灵缶之中,没有主人的命令不可擅自行动,莫说自断灵羁,理应连接近宿星潭都不能。然而,就是在这种种不可能之下,她永远失去了那少年……通往宿星潭的路并不曲折,脚下平铺的青石板光洁平整,唯有角落的缝隙中,染着些微苔痕。那一夜,是怎样的月色?那走过这段路的少年,是怎样的心情?可曾有那么一瞬,他想过回头?而今,那温柔的神尊,是否也选了同样的路?是不是无论她如何尽力挽留,她所珍惜的皆都要离她而去?冉悦走得很快,越来越快,片刻便从小跑变成了拔足狂奔。思绪,陷入一片哀切的迷惘。一时间,她竟不知自己追寻是辰霄,还是燕还,又或是那永远无法倒回的时光。混乱之间,宿星潭近在眼前,冉悦茫茫然想上前,却不防两道身影飞纵而下,挡住了她的去路。“放肆!”来者斥骂了一声,道,“竟敢擅闯宿星潭!”惊吓之间,冉悦醒过了神来。眼前那二人,她并不认识。但看衣装,应该是镇溟坛的弟子。她略估摸了一下那二人的年纪,恭敬道:“二位师兄,能否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宫主有令,擅闯宿星潭者,门规处置。”先前斥骂了她的那位弟子厉声说道。宿星潭虽是门派圣地,却从未禁止弟子出入。冉悦一时有些不解,正想问询,却听另一个人开了口,笑道:“等等,这位不就是宿星潭被封的始作俑者么?难道说,好不容易牺牲自己的战灵换得了神尊,却不想那神尊竟变作了凡人,所以就来再召唤一个不成?”这番话中虽带着笑意,却满含讥嘲,听来甚是刺耳。冉悦心里不是滋味,却终究没有反驳。想来越无岐对她不善,她门下的弟子这个态度也不奇怪。是非对错,自有公论,又何苦针锋相对。现如今,找到辰霄才是第一位的。她想了想方才听到的话,问道:“二位师兄既守在此处,就是说,不曾有人通过这里,对吧?”这话问得奇怪,那二人对望一眼,依旧是那含笑的弟子开口应答:“这是当然。”他说着,踱步到了冉悦面前,“其实除了你,也不曾有人来过。你换得神尊之后,宫主担心有弟子效法,也命自己的战灵入潭殒身,方才下了禁令。可本门之内,哪里又有那么多不肖弟子呢?”冉悦只觉眼眶发酸,似乎又要落下泪来。她忙低头行礼以作掩饰,又忍着声音里的哽咽,道了一声谢,转身离开。无论如何,确认辰霄未曾来过,已经足够了……她停了步子,略微抬头,努力将眼泪憋了回去。今天已经哭得够多了,不该再掉这些无谓的眼泪才是。她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挤出一个笑容来,权当给自己加油鼓劲。如此振作了一番,她才继续往前。只是,没有来宿星潭的话,他会去哪里呢?被谁叫走了?可门派之中,除了宁疏和宏毅,他并无相熟的人,又有谁会找他?难道,是越无岐?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还是决定要毁掉他体内的神桑金蕊?……一时间,她的脑海里满是乱七八糟的念头,倒把一番委屈和悲伤抛在了后头,只余了担忧和慌张。到底还是该找人问问才是!她不敢耽搁,又小跑了起来。然而,也不知是早上那场“切磋”耗空了体力、还是情绪起伏费尽了精神、又或是大半日不曾饮食而致的体虚气乏,她只觉双腿愈来愈沉重、呼吸和心跳亦开始紊乱,难言的疲惫逐渐蔓延全身,令她无力起来。终于,她停了下来,扶着道旁的大树,不定地喘气。已是初秋,夜风微凉。因为奔跑而起的汗水,经这凉风一吹,顿生寒意,惹她微微颤抖。她闭目,想略养一养神,却不防身子一晃,直接靠上了树干。竟连站都站不稳了么?她自嘲一笑,慢慢站直了身,正要继续往前,却听一声温柔的呼唤:“主上。”那时那刻,这一声呼唤听来虚实难辨。冉悦迟疑了一下,方才顺着那声音抬起了头。青石长径,被轻巧踏过。走到她面前来的人,披着一身月色,亦有种似假还真的缥缈。待他伸出手,扶上她的肩膀,将满掌的温暖相递,她方才确证他的真实。一涌而上的安心和踏实,令她骤生出些不争气的软弱。她由着自己的无力,顺势靠上他的肩头,手抓着他的前襟,半带抱怨地问:“去哪儿了?”辰霄见她这般,不免有些担心,又听她问,便老实回答:“去演武场练剑,又去后山冲了凉……主上在找我?”练剑、冲凉……似乎曾经也听过相似的话。冉悦埋头在他肩窝,翁着声道:“太晚了……”辰霄只疑是自己晚归惹她不悦,忙解释道:“今晨是因我无能,才令主上输了那一局。如今灵羁被阻,我能做的也只有练剑。我基础太差,若要提升,唯有勤练,所以才多耽搁了一会儿……”他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什么,怯然问道,“我方才回去,见主上不在,天色又晚了,所以才……主上说了要一个人静一静,我是不是打扰——”他的话还未说完,冉悦松开了抓着他前襟的手,转而将他紧紧抱住。辰霄一怔,忘了言语。她抱得太过用力,令他隐隐生痛。但他并未抗拒,更不提挣脱。他只是抬手,轻轻抚上她的后背,疑惑着问了一声:“主上,怎么了?”冉悦沉默了片刻,似乎发觉了什么,略微放松了自己的力道,却始终没有松开手。她迟疑着,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我以为,你去了宿星潭……”“宿星潭?”辰霄略想了想,立刻明白了过来。他浅浅笑着,出口的话语平和而又恳切,“主上不必担心。诚如绝斩所言,我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弱之徒,绝没有自断灵羁的胆量。”这些话听来像是半带调侃的安慰,但辰霄却绝对不是会如此调侃之人。冉悦想到这里,松手退身,望着他的眼睛,气道:“什么贪生怕死,什么懦弱之徒啊,那是绝斩胡说八道,我都替你骂过他了,你怎么还这么说自己!”辰霄见她如此反应,笑道:“多谢主上袒护。可事实就是事实。”冉悦哪里能领这句谢。她抬手轻捶了一下他的胸膛,紧皱着眉头道:“都说了不许这么说。”辰霄依旧笑着,语调亦是惯常的温软:“主上虽不许,但有些事,我还是要告诉主上。”他低头,抬手覆上冉悦的手,低诉的话语里染着难以察觉的怅然,“只要主上不断开灵羁,我便永远都不会离开。纵使无能,拖累主上,也不会离开。主上要我做的事,无论什么我都会做。剑术或者道法,必都竭尽所能……”他说到此处,言语一哽,而后的那句话,听来竟似自责,“对不起,我终究,比不上燕还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