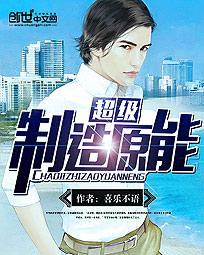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独占金枝人物介绍 > 第四百八十二章 动手5K(第1页)
第四百八十二章 动手5K(第1页)
季崇言看向姜韶颜,眼见女孩子朝他点了点头,他这才转身去后头“出恭”去了。
待到季崇言走后,掌柜干笑着看向女孩子:“小……小姐,您这是……?”
“闲聊啊!”女孩子看了他一眼,抓了块干果点心盘子里的糖饼咬了一口之后,复又提笔,下笔“簌簌”几笔开始边画边道:“他‘出恭’怕是要一两个时辰,我们聊聊。”
有什么好聊的?掌柜暗忖:你二位上门又不是买成衣的,是问话的,眼下他把压在心底里的话都掏空了,还有什么好聊的?
只是虽是这般暗忖,可到底人微言轻,对方又是那等贵人身份……掌柜翻了翻眼皮,在肚子里搜刮了一圈之后,找到了一句夸赞之词:“小姐画技真真不错,惟妙惟肖的!”
正下笔“簌簌”画着的女孩子闻言抬头看了他一眼,笑道:“我也觉得。”
掌柜:“……”
这么聊天的吗?不是应当谦虚一二,而后他再夸赞,她继续谦虚,如此一番废话,啊呸,这怎么能叫废话呢?这叫寒暄!总之,如此寒暄一番过后,估摸着那位“出恭”也该回来了。
只可惜眼前这位不大会聊天,掌柜叹了口气,正想继续开口,那厢“簌簌”下笔的女孩子却已放下了手里的笔,吹了吹自己寥寥几笔画的大作,上下颠倒了一下放至他的面前,道:“掌柜是个趣人,还挺对我胃口的,便送你一份见面礼好了!”
素白的纸张上寥寥数笔,一个头戴冠帽的蓄须掌柜的模样此时已跃然于纸上,纸上之人实在是太过眼熟,每日晨起睡前照镜子时,他都能从铜镜中看到那张脸。不是他的,还能是谁?
前一刻还在感慨这位小姐若用这般迅速生动的画技来帮衙门抓嫌犯倒是一画一个准,眼下自己却已率先出现在了这画纸之上,掌柜莫名的有些心虚的同时还有种古怪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画像出现在纸上跟个嫌犯似的。
面前这位“和善”的小姐倒是浑不在意,哄孩童似的大方的送了他一副见面礼,掌柜干笑着,在女子“和善”的笑容中收下了见面礼,客气的连声道谢。
“谢就免了。”女孩子摆了摆手,看了他一眼,再次出声,说了一句让掌柜心惊胆颤的话:“掌柜真是个机灵的,我倒是有些想将掌柜请去长安替我管铺子了。”
姜兆早早便为她在长安留了两间铺子,虽然地段不算顶好,可因着在长安的缘故也值些钱财。因着原主并不喜欢理会这些俗事,那铺子便租赁了出去,收些租钱。
如此个厚爱法险些没把掌柜吓了个够呛,连连摆手道:“不……不必了!我愚笨的很,在洛阳这里讨讨生活便好,长安便不去了。”
女孩子看着这掌柜避之不及的模样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转而继续同他闲聊了起来:“你是洛阳当地人?这一口洛阳地方口音听着挺地道的。”
掌柜老老实实的摇头道:“倒也不是,我祖籍在岭南呢!家父从岭南来了洛阳这等大城讨生活,我这才得以在这边出生。因着一出生就在洛阳,所以也只会洛阳话,并不会岭南话。”
“先时怎么想到当药铺掌柜的?”女孩子打量着他,接着问道。
掌柜道:“家父在岭南本是种药田的药农,虽然不算正经医馆学徒,可因着种药,不少药材也认得出来。来洛阳之后,便靠着辨药的本事在医馆做学徒什么的,待我出生,家父在医馆也算是个还会帮着算账的医馆小管事了。”
当然,这等医馆小管事也就管个账同几个学徒而已,同王家这等大族的管事不可同日而语。
说起往事,掌柜语气中倒是多了几分感慨和唏嘘:“日子总是一代一代人努力的结果,若没有家父这个医馆小管事的身份帮忙,我也做不得这大掌柜!”
他一个小小的铺子掌柜都是父亲与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更遑论那些大族了。
女孩子笑看着他,没有接话,只是转而问他:“你父亲是岭南药田的药农,他种过麻蒙草?”
掌柜听的迟疑了一刻,这两位贵人今日自进来开始问的话便没有离开过“麻蒙草”这三个字,只是略一迟疑,想着总是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是以他还是点头道:“是啊!家父种过不少药田,其中就包括麻蒙草。”
姜韶颜道:“那你父亲当年在岭南是为什么人种的药?东家是谁?”
“这个父亲没提过,”掌柜皱了皱眉,说道,“不过当年岭南的大药田都是冀州叶家的,想来父亲也是为叶家种的药草。”
“你如今五十上下……你父亲当年种药的时候当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不曾听说岭南发生过什么战事灾荒之事,那你父亲为何舍了药农的活计离了家乡千里迢迢来洛阳讨生活?”女孩子笑问他。
这话问的掌柜眉头蹙的更紧了,他面上闪过一丝茫然与疑惑之色,顿了片刻之后,摇头道:“这我便不知道了,父亲不曾说过,许是当时年轻,想多赚些银钱搏一搏什么的吧!”
这些他从未想过,如今他父亲也已过世许久了,想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骤然提起过世的老父,掌柜心情也不算太好,忍不住扶额,懊恼道:“早知两位贵客要问这么多,当时您二位问我麻蒙草的事时,我真真说什么都不会承认的了。”
本是一句抱怨话,岂料这话一出,那位“和善”的女孩子便笑道:“掌柜当庆幸你说了实话,你当时若是不承认,眼下早已被我二人带走,不会还能坐在这里同我闲聊了。”
便是因为这掌柜没有隐瞒麻蒙草的事情,所以她同季崇言笃定这位并不知晓内情,否则自是要带回去审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