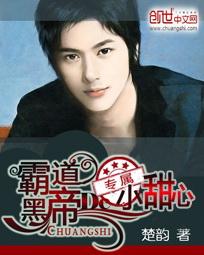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喜马拉雅兀鹰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ldo;好,你是个禁欲主义者,是吗?&rdo;
&ldo;在一月四日之前是的。&rdo;
梅森笑着走了过来。&ldo;好了,姑娘们!咖啡来了,还有三块巧克力,怎么样?&rdo;
&ldo;节食只有从明天再开始了,是吗?警官。&rdo;
&ldo;就算是吧。弗拉德我告诉你,我正为下星期天的十公里长跑补充碳水化合物呢。比赛要在树林边的小镇举行。&rdo;
&ldo;齐切斯特?&rdo;
&ldo;没错。&rdo;
&ldo;太好了!&rdo;
三人喝着咖啡,莫伊拉和梅森把凯茨的巧克力给分了。当凯茨抬眼偷看了莫伊拉一眼,她顺过头来对着她笑,棕黄色的眼睛大大的,说:&ldo;没有事,凯茨!&rdo;
梅森又有新情况了。&ldo;我在楼下和几个人说了会儿话。其中一个是裁判,对不参加联赛的球队知之甚多。我问他穿黑色和琥珀色球衣的球队,你想知道有多少个吗?&rdo;
&ldo;不太想知道,但你要告诉我,是吗?&rdo;
&ldo;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四个队,我的伙伴告诉我有九个队穿黄和黑色球衣的,一个队是琥珀色和海蓝色球衣,另外还有几队穿黑色和琥珀色球衣。&rdo;
&ldo;真见鬼!&rdo;
&ldo;这只是当地的球队!除去新港队,赫尔斯市队和狼队,南港队和东图洛克队,伊塞克斯队不计在内,还有……等一下,我写在了一张纸上,在哪儿呢?按地理顺序,班斯蒂德运动队,科文队,哈范特城队,沃金汉姆队,纽伯里队,特鲁布莱奇队,威尔特人队。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的的马龙队和斯劳队。&rdo;
凯茨看起来有点欣喜若狂。
&ldo;实际上,斯劳队穿蓝色和琥珀色球衣踢球的……还有许多连联盟手册都没有的小俱乐部,如萨里的贝辛斯托克队和白叶队。他们的备用球衣也是黑色和琥珀色的。&rdo;
&ldo;帮我个忙,警官。&rdo;
&ldo;请讲。&rdo;
&ldo;如果再碰到懂足球的人,不要再问他什么东西了。&rdo;
&ldo;我知道你很高兴,弗拉德。这就是个好警官应该做的,不是吗?&rdo;他咬了口巧克力,那是凯茨的。
&ldo;我能扫一眼那张纸吗?警官。&rdo;
&ldo;愿意为您效劳。&rdo;
凯茨拿了名单问他们可以走了吗?接着她笑了笑,突然用刚学会的威尔士口音说:&ldo;我们去找加雷斯谈谈。&rdo;
15
加雷斯&iddot;博克斯给了他们一个很容易找到的地址,在南安普敦的贝福德附近的格罗斯夫诺广场。紧挨在它后面的是原先的公共汽车站,现在已经被办公楼取而代之。他们开着瓦莱丽的戴姆勒向右转弯,对面是一排餐馆,接着绕过路易勒&iddot;蒙巴顿伯爵的铜像。十一点钟以前的贝福德是怡人的,十一点三十分后就成了臭名照着的嘈乱之所:回家的食客们吃着鱼和油炸土豆片或是除掉智利香料的羊肉串,喷着酒气,熙来攘往。蒙巴顿伯爵的铜像居然还能屹立不动,凯茨不由得心生疑虑。
&ldo;有碍观瞻。&rdo;彼得嘟囔一句,车很快就开过去了。
博克斯所住的三层楼房是这个新街区里最大的一幢公寓,公共花园修剪得整整齐齐,喷泉嘶嘶地喷着水。博克斯住在顶层。每到周六晚上花园里都会云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打闹喧哗,但三层楼的隔离已足够让他保有自己的清静。为了见到他,三人不得不穿过两道门,绕了建筑物一周,隔着格子网和他打了招呼,然后再挤上电梯。当发现自己和两位女士面对面站着时,梅森微笑了。凯茨身体前倾去够操作按钮,终于按到了&ldo;3&rdo;,可前臂却碰到了梅森堆满灿烂笑容的面颊。
&ldo;你们好!&rdo;博克斯说,一下子打开门,弯了一下腰,把三人领进屋。一看见他,凯茨就看出,&ldo;他刚和人做过爱。&rdo;随着其他几个人走进公寓,她还纳闷,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想法。整个客厅都弥漫着煮沸的咖啡豆的香味。梅森走在前面,突然在休息室前停住了脚步。莫伊拉反应不及,一头撞到了梅森的后背上。
&ldo;请进,我正在煮咖啡,上等的巴西货。是不是挺诱人的?&rdo;
凯茨最后一个进门,一跨进门就立刻明白了刚才队伍排头的人为什么会犹豫了。房间很简单却不由得让人吃惊。左边一堵墙直竖着有二十英尺高。从那里,镶着松木的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外墙上,离地板也有九英尺,然后像瀑布一样略带角度地倾泻到地板上,在这面斜墙顶上有五个铜边的窗户。
他们进来时,灯开着,显然是为了营造气氛。休息室大约有四十五英尺长,天花板上淡棕色的条纹,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奕奕生辉,中间离房间的最低端三分之一处有一块坚硬的灰白色大理石,发着光泽,作为咖啡桌。上面,随意放着一架银灰色的哈苏相机,长镜头,一个曝光表和红色的小笔记本。从远处的的某个地方传来博克斯先生的声音,让他们坐下。莫伊拉和梅森各自找了一把有白色皮垫的低椅坐下。但是凯茨还是站着。
&ldo;我站着你不介意吧?&rdo;博克斯先生一进门时她就迅速问道,&ldo;我一整天都坐着,我想站着活动一下手脚。&rdo;
&ldo;请便。&rdo;博克斯说。
&ldo;我是弗拉德警官,&rdo;凯茨正式地说,不露痕迹地用鼻子做了一次又长又慢的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