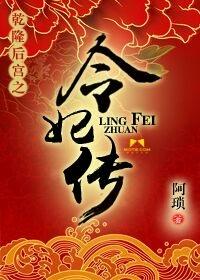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喜事游戏安卓 > 第4章(第2页)
第4章(第2页)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二儿媳妇把离婚协议书疯狂地撕了个粉碎,尖叫着冲到宗祠,对着禁闭的大门拳打脚踢。
&ldo;死老头子!把我的钱吐出来!全都吐出来!&rdo;
她离了婚,那两兄弟找不到人,范宅易了主……她什么都没得到!
看热闹的人分外疑惑,看这女人撒泼打滚的气势,疯劲倒有,傻劲哪里有半分。
片刻后又恍然,看来为了不离婚,果真故意装疯卖傻。
门内的宗祠公悠悠地喝着茶,嗤笑着,&ldo;人心不足蛇吞象,蠢女人啊,没真疯就该求神拜佛了,还要钱,老子让你一无所有!&rdo;
月色皎皎,树叶沙沙。
二儿子躺在床上,脸色红润,唇角挂着安心的微笑,似乎在做着什么美梦,意识朦胧间,有个熟悉的气息纠缠上来。
微凉的手剥开他的衣服,抚摸,揉捏。
柔软的唇亲吻着他的肌肤,啃咬,舔舐,每一次碰触都恰到好处地落在了他的敏感点上。
他情不自禁地低喘着,暧昧的痛苦又欢愉。
那股亲昵急切起来,在他全身上下肆虐着,进攻着,硬物抵住了入口,推挤着,他痛得皱眉,柔软的唇捕捉过来,吞进了他的痛呼。
硬物缓缓动了起来,不疾不徐,慢条斯理地享受着猎物‐‐
二儿子霍然睁开眼。
眼前一张放大的脸,一张父亲年轻时的脸。
一张让他畏之如虎,恐惧至极的脸。
也是……大哥的脸。
&ldo;是……你。&rdo;他生生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ldo;一直……都是你。&rdo;
伏在他身上的人啄了他一口,笑了笑,&ldo;我亲爱的弟弟,当然是我,别担心,你很干净,一直很干净。&rdo;
十几岁时那很多个夜里,他被捆绑着手脚,蒙着眼,受尽屈辱折磨,原来全是拜这个人所赐。
幼年时亲眼无意中目睹父亲禽兽的行为,让他自发地为那些事找了凶手。
他恨,恨大哥把自己曾经承受过的痛苦,十倍百倍地施诸他身上。
不……他像缺水的鱼一样张开了嘴,却无法呼吸。
不……他徒劳的反抗在猛烈的撞击里被冲得七零八落,最终化作月光下的纷飞的尘埃,消失在空气里。
昏暗的墙角里,痴痴傻傻的小男孩流着口水,含糊不清地咕哝,&ldo;爹爹像爷爷,爷爷像爹爹,哪个是爹爹,哪个是爷爷啊……&rdo;
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忽然对着空气哭喊,&ldo;妈妈妈妈,爹爹脏,爹爹好脏,给爹爹吃毒糖糖……&rdo;
喊着喊着,他又害怕得缩成一团,&ldo;婶婶,婶婶,我很乖,我很听话,不要给我吃毒糖糖,好痛好痛……&rdo;
大儿子近乎虔诚亲吻着身下这具让他着迷的身体。
漫漫长夜,他怀有至宝,怎会虚度春宵。
怀里的至宝似乎认命了,不声不息的,木然地望着天花板,神色里透出一股死寂来,连绝望都看不到。
大儿子皱了皱眉,他的性趣并不在于奸尸。
听见幼子的哭闹,他眯了眯眼,莫名觉得烦躁。
下了床,走到墙角,儿子对上他的视线,哭声立止,惊恐地贴住了墙。
大儿子满意了,毕竟是他儿子,只要听话,养着也没什么。
重新回到床上,弟弟仍旧是那副任人鱼肉的麻木表情。
舔了舔唇,突然觉得眼前景致无限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