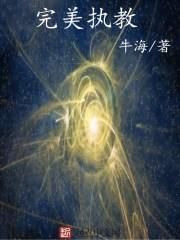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穿到权臣年少时梁北音 > 第264页(第1页)
第264页(第1页)
楚汀蕙脑中嗡声一片,眼眶倏然泛红:“怎么会……侯爷向来德行高洁,定然知道汀蕙所行皆为大义,侯爷岂是那等肤浅之人?”“那本侯只能说一句,楚医女看错了。”楚汀蕙将下唇咬得泛白:“不可能……我不信……前日侯爷分明还在百姓面前夸过我蕙质兰心……”“那只不过是为了安抚沧州百姓情绪罢了。”段长暮不屑地冷笑一声,“楚医女该不会把这种话当真了吧?”楚汀蕙连连摇头:“若是侯爷不喜欢,汀蕙今日起就不再抛头露面去给百姓施粥……”“楚医女,本侯以为你不是愚蠢之人。”段长暮冷冷地看着她,“真要本侯命人将你送走,你才能明白本侯的意思?”楚汀蕙望向他,察觉出他眼底浓厚的威胁意味,不由吓得打了个寒噤:“是苏校尉让你这么做的?”“与他无关。”段长暮移开眼神,示意望舒送客。“侯爷这么宝贝她,可知道她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楚汀蕙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矜持,放声质问,“侯爷看不起女子混迹于军营,将来可别打自己脸才好。”段长暮眉尖微蹙,下意识反感她这番说辞:“楚医女,本侯看在你为沧州百姓的付出上,已经足够容忍你了,你再这么口无遮拦,休怪本侯无情。”望舒见段长暮震怒,赶忙连拉带拽地将楚汀蕙请了出去。楚汀蕙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眼底满是阴狠的恨意,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叫段长暮后悔今日这般对待自己。—沧州的灾后重建工作要比所有人想象中更难,古代医疗条件差,卫生环境堪忧。虽然苏平河极力劝阻灾民们喝生水,但还是架不住总有那么些人不听劝。瘟疫来得又急又快,沧州城很快变成了人人自危的人间地狱。侥幸逃脱地震灾害的幸存者们好不容易才重拾了几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又被现实无情地击倒了。苏平河心急如焚,几乎是一有时间就在翻看方蝉衣的那本医书。这本医书的设定就是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决古代疑难杂症,不应该没有针对疫症的治疗方案。只可惜,这本书实在太厚了,饶是一页一页翻过去,苏平河也要花上许久功夫。“早知道这些年我就不应该偷懒,每天为你注释一页,现在就不至于临时抱佛脚了。”方蝉衣见她双眼布满血丝,心疼得不行:“你别着急,总能找到的。”苏平河揉揉眼睛:“如何能不着急,城中百姓半数都被感染了……我就怕,再不找出方子,连你我都难逃此难……到时候就更没办法了。”“不会的。”方蝉衣看着她,又强调了一遍,“不会的。”苏平河依照自己在现代见过的防疫经验,在纸上罗列出数条注意事项:“药方还没研制出来,目前最要紧的是控制疫症扩散,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法子。”方蝉衣接过看了看:“掩住口鼻这条我也想到了,集中管制只怕有些难度……”“段长暮会有办法的。”苏平河不假思索地说,“你拿去给他瞧瞧。”方蝉衣应声走了出去。苏平河用凉水擦了把脸,继续一页一页翻着医书。段长暮果真如苏平河所言,对城中百姓实行了犹如军事化的管理。他本身性格就冷漠至极,下达的命令刚有反对的苗头,就被他强硬压制了。“少主,已经按照您的指示设置了隔离点,城门也落了锁,只进不出。”望舒顿了顿又说,“只是…城中百姓怨声载道,咱们的人马先前攒起来的好名声,这几日全没了……”段长暮不在意地挑眉:“本侯何时在意过名声?”“少主从来不在意旁人怎么说,可是……”望舒欲言又止地看了看苏平河所在的位置。“说他什么了?”段长暮想到苏平河连日来只睡一两个时辰,熬得眼下一片乌青,心里就像被揪着一般,容不得别人说他半句不好。“百姓们说他蛇蝎心肠,想把全城的人都困死在沧州……”“一派胡言!”段长暮猛地拍了下桌子,“好好的怎么会有这种传言出来?沧州百姓如何能认识他?”“属下去查了查,发现谣言似乎是楚姑娘散布出去的。”段长暮脸色铁青:“你现在就把她给我赶出城去!”“少主……沧州城已经只进不出了……”段长暮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苏平河忽然拿着一张方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我找到了!对付疫症的方子!”方蝉衣眼前一亮,赶忙伸手接了过去:“真是太好了!”苏平河虚弱地笑了笑,忽然腿一软就倒了下去。段长暮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她的腰身,疾呼:“方大夫!”方蝉衣顾不得药方,赶忙去帮苏平河把脉。片刻后,他神色凝重地说:“还请侯爷暂避,公子她……似乎也染上疫症了……”货真价实的女人段长暮瞳孔猛地一缩,当即便下令道:“你们都出去。”知道段长暮是想亲自照顾苏平河,望舒急坏了:“这如何使得?”“本侯的话也不听了?”段长暮神色一凛,“左右药方已经找到,没什么好担心的。”望舒无奈,只好跟方蝉衣退了出去:“方大夫,您可千万得抓紧时间把药研制出来啊……”方蝉衣神色凛然:“放心,方某不会拿公子的性命开玩笑。”苏平河觉得自己口干舌燥,头昏脑胀,想要开口说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声,眼泪都急得流了出来。段长暮拧干帕子帮她轻轻擦拭着额头,紧锁的眉头就没舒展开过。“等沧州的事处理完了,我就带你回京。”段长暮喃喃道,“你这样的身子骨,哪里经得住西北的气候?从我在军营里再见到你开始,就没有几日是活蹦乱跳的……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非来受这个罪。”苏平河听着他絮絮叨叨的声音,第一次觉得段长暮原来也有话痨的一天。她勉强着睁开眼睛,张了张嘴。段长暮见她眼底一片血红,心疼得不行:“不多睡睡,又醒过来做什么?口渴了?”苏平河摇摇头,表示自己想坐起来。段长暮只好将她扶坐起身,斜倚在软枕上。“你怎么不掩住口鼻?”苏平河听到自己的破锣嗓子在问,“非要把自己也给染上疫症才罢休吗?”没想到某人竟然点了点头:“是的。”“什么?”“我想跟你同甘共苦。”苏平河瞪大了眼睛。怎么,段长暮拿的原来不是杀伐果断冷血无情的男主脚本,而是个恋爱脑人设?这一瞬间,苏平河忽然不想跟自己较劲了。他如此珍爱她,连疫症都不避讳,又岂会因为她是女儿身就厌恶她?她闭了闭酸涩的眼睛,下定决心开口道:“段长暮……我跟你说……我其实不是个男人……你信吗?”谁知,段长暮的反应却是摸了摸她的额头:“果真烫得很,都开始说胡话了……”预料之中的感人画面,或是错愕画面都没出现。画风开始逐渐离奇。段长暮竟还暗自嘀咕道:“难道染上疫症会让人产生幻觉?”苏平河眨了眨眼,呆愣片刻后冲他摆手:“怎么是说胡话呢,我没有说胡话,我是认真的……”段长暮深深凝望着她,了然地点点头:“我知道。”听他这么说,苏平河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一直因为我们都是男子的事耿耿于怀,这才会幻想自己如果是女子就好了……”他说着竟然还动容地将苏平河一把揽进了怀中,“平河,没关系的……我早就接受我心悦之人是男人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