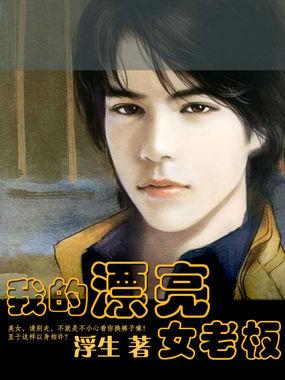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残疾人宣传稿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电视机是个好东西,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柳青爬上门前的柳树,把天线绑在最高的树枝上,戏子在下面喊,有影了,声音也有了!到晚上,村里的人也来看电视。男人们蹲在地上呼啦啦的喝面条,老娘们坐在墙根哼哼唧唧的哄孩子。
人类相处的多么融洽!
小拉一边看电视,一边搓泥。他搓完脖子搓脚丫,搓成一个泥丸,他闻闻(香?),嘿嘿一笑,就向那老娘们堆里砸了过去。这是一种调戏,也是爱的表达方式。几个老娘们也把小石头扔过来,笑嘻嘻的说,丢你娘的绣球。绣球二字使小拉想入非非。这单身男人下劲搓了个大的,砸中了一个寡妇的头。那寡妇一拍大腿破口大骂,哪个小歪逼?小拉站起来说是我,寡妇扭扭屁股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三巴掌。众人哄笑起来。小拉摸着自己的头,看着女人的手。除了他娘,还没有别的女人碰过他。
叶子是个淘气的小姑娘,在我记忆中她的裙子永远是脏兮兮的。她在人群里挥舞着一把小勺,嘴里嚷着打,打。柳青躺在摇椅上说,不听话,打屁股。叶子说打。柳青便在她屁股蛋子上来了一下,问她还打不打,她嘴一撇,说抱抱。
我爹抽着旱烟,我娘攥着根绳子。我爬到东,爬到西,看看哪个好心人能喂我几口。我娘把我拽回来放在膝盖上,她小声哼唱:
月老娘,黄巴巴,
爹浇地,娘绣花。
小乖儿,想吃妈,
拿刀来,割给他,
挂他脖里吃去吧!
她想把我哄睡,自己却迷迷糊糊睡着了。我爬到大门口,坐在那里看呼啸而过的车辆。那一刻我很孤独。一个人从公路上走过来,拐弯在我面前停下。他的脸恐怖极了。我吓的双手抱着头不敢说话。终于,我一声嚎叫。当时正是夏夜,电视机前的人们扭头看到那张脸也都打了寒颤。
那张脸简直就是魔鬼的杰作。他的脑袋缩在肩膀里,一截僵硬的脖子露着青筋,喉咙肯定结扎过,咽口唾沫要费很大的劲。两腮写着狰狞,额头上伏着一只癞蛤蟆,翻转的耳朵会引来风暴,有悲惨的声音在里面回响。该怎么称呼他的鼻子呢,一个小疙瘩?一个卵?一个瘤?牙齿是撬杠,嘴唇成了支点,而嘴角塌陷着,随时都可能流出白沫,那下巴,那下巴却怪异的翘了上去,形成一个酒窝,几滴雨和汗可以储存在那里。杂乱的五官只剩下一只眼还活着,眼皮上翻露着血丝,惊恐的眼球突出,仿佛一耳光就能震落,另一只眼死的很难看,眉毛在深陷的眼眶里象是黑色的小糙。整张脸树皮似的疙疙瘩瘩,坑坑洼洼,只有眉间的一小块皮肤是完好的,憎恨和丑陋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一小片柔情又有什么用呢?(随风去吧!)
伙计,脸咋啦?柳青问。
烫的,开水烫的。他回答。
当天夜里,我娘对我爹说,新来的这个人,我认识!
这个人就是那个卖包子的小贩。生活中处处隐藏着危险。一锅沸水从天而降,他的人生断成两截。上半辈子是天堂,下半辈子是地狱。命运把他折磨的不成人样。他象一个鬼,白天不能出来,晚上化做一个游魂,孤孤单单。对这具行尸走肉来说,苟且偷生有什么不好呢?(good)
不要脸才能生存,没有别的办法!
柳营是唯一能医治他痛苦的解药。残疾使他们一律平等。他姓马,是个回回,小拉也是回回。安塞俩木尔来困(求真主赐予您安宁)。俩易俩海,因兰拉乎(万物非主,惟有安拉)。一个回子撑死,两个回子饿死。他和小拉都遵从了穆斯林的饮食习惯。吃饭是一种享受。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马回回熬了一大锅羊汤,熬了三天三夜。雪花飞舞,香味弥漫。他对小拉说,单县有口锅,三十多年没熄火了,慢慢炖着,咕噜咕噜,那汤熬的,木头掉锅里嚼着都香。小拉咽口唾沫,单县,莱芜,西安的羊汤好喝。马回回讲了一个故事:黄河边有个老头,有一年发大水,老头和三个儿子牵着羊扛着家什就到山上去了。从水里漂过来一个药箱,药箱里有十三种中药。老头不能饿着等死啊,就把羊宰了,用那十三种中药熬了一锅汤。香味引的老鼠呀蛇呀,都围着锅乱转悠。老头说,家淹啦,屋子也塌啦,喝完这锅汤,就各奔东西,去要饭吧!洪水退去,三个儿子打了个饱嗝,一个要饭去了西安,一个去了莱芜,另一个去了单县,后来都开了间羊汤馆。(老头呢,饿死了?)那十三种中药就成了秘方,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我在单县偷偷学了三年,才学会这手艺。浇上辣椒油,撒上香菜,我爹喝了五碗,我娘喝了三碗(给俺留点)。柳青擦擦额头上的汗,说过瘾。戏子说,马回回你该开个小饭馆,咱这里,戏子在地上画,南边是获麟街,北边是327国道,咱就在这俩十字路口中间,进城出城都得经过这,马回回,你该开个小饭馆。马回回说,我以前就是干这的。柳青说在门口搭个棚子试试吧!
感谢天时,地利,还有人和。鞭炮声过后,马回回的小饭馆开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棚子,搭在公路壕上面,不是傻bi少女幻想的那种小木屋,它阴天漏雨,刮大风时摇摇晃晃,但它的出现标志着残疾人事业迈出了很大一步。
这一步,是翱翔的开始!
我五岁那年送给马回回一个面具。那时我已经会走,拖着右腿,口袋里有三颗弹珠,每走一步都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脚是路的梦。这里有朵小花,那里有堆狗屎。我不能因此而停下脚步。大步走路大声说话大口吐痰大碗吃饭大瓢喝水,我娘认为这才是男子汉气概。我是个瘸子,所以我当不了男子汉。
在一棵树下,我用三颗弹珠中红色的那颗赢了一个面具。我对那个输了的小孩说,你的枪法也很准。小孩坐在地上哭起来,骂我臭瘸子。叶子说,小狗骂人,掐死你。那小孩哭的更厉害了,叶子向他吐舌头,做鬼脸。
我把面具给了马回回。我娘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他犹豫了一会,慢慢的戴上,整个人立刻焕发出耀眼的光芒。神佛也不过如此。光芒来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文化,那是张脸谱,生旦净末丑中的一个。那色彩亦是神采。多么美妙的戏剧转折!他站在那里,站在人生的舞台。往前一步走向新生,退缩一点就是王八,举头三尺便有天理,脚下则是人道。(前进!前进进!)马回回的饭馆越来越红火。有了第一,就有了第二。一年以后,紧挨着马回回的饭馆又开了间诊所。开诊所的是个瘫子,叫安生,中医世家,山东平阴人。安生18岁那年遭遇电击,两条腿废了,因为忍受不了周围的歧视与冷落,他25岁毅然离家出走。江湖路远,他若不知,生足何用。自由象天地般宽广。他在别人的屋檐下躲避雨雪,夏天露宿街头,冬天睡在路边的塑料大棚里。安生在集市上卖膏药,有个卸白菜的司机告诉他嘉祥县柳营有个编筐的厂子,那里干活的全都是残疾人。他听说之后就去了柳营。
一天傍晚,狂风扫净了落叶和塑料袋,留下一条干净的公路等待着大雨的来临。马回回,大头,家起都在饭馆里围着炉子烤火,戏子和柳青坐在桌前喝茶。屋外雷声滚滚,一个人进来了。他是爬进来的。
这个人就是安生。他的屁股下绑着烂轮胎,两只手都套着破拖鞋,脖子上挂着一个很旧的人造革的皮包。安生抬脸看看屋里的人,这里就是柳营?柳青说是。安生两手撑地向炉边蠕动了一下,歇歇,总算到了。戏子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平阴,又拍拍屁股下的轮胎说,这一路磨烂了八个。马回回盛了碗羊汤放在安生面前的地上,安生翻开口袋,摊着两手说,没钱。马回回说,喝!
安生便捧着碗,吹着热气,一边喝,一边说,天真冷,肠子都快冻僵了,这汤熬的还行,火候差点,汤里放了花椒,大茴,丁香,白芷,桂皮,豆蔻,砂仁,山奈多了,良姜少了,有黄连就有厚朴,还有胡椒和当归,一共十三种中药。马回回很震惊,心里想这是遇见高人了。他问安生咋知道的。安生抹抹嘴说,俺走江湖,卖膏药,懂点中药材,看,他从胸前的包里拿出两贴膏药,一块钱俩,敷肚脐,治百病。大头走过来将那膏药闻了闻,屁,骗人的玩意。家起说,治百病,我这腿能治不?安生敲敲家起的小车,柳木的,活腿能治,死腿治不了。啥叫死腿,家起问。安生打了个饱嗝,从包里拈出一根细长的针,插在自己腿上说,看,这就是死腿,没反应。他又把针拔起来,打着火机烤了烤,然后猛的扎在家起的大腿内侧,家起疼的哎呦一声直咧嘴。安生说,你这就是活腿,嘿嘿,有反应。能治好不,家起揉着腿问。安生把针放回包里,日天的本事也治不好,不过能让你站起来。家起很激动,抓住安生的手说,要能站起来,我给你跪下磕头。安生一笑,说不用,你这小车不错,到时给我就行。
三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家起喊了一声救命啊!这声音在夜里听起来毛骨悚然,就象刀划破了玻璃。小拉拉着电灯,宿舍里的人看到家起竟然站起来了,他扶着床栏看着自己的腿,脸上的肉直打哆嗦。他慢慢向前挪了一点,大滴的泪砸在了脚上。几天后,家起借助双拐终于能够直立行走,他由一个猿,或者说一个畜生,一个野兽,一只爬行动物,而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太字!)
为了表示感谢,家起托柳青买了一辆轮椅送给安生。他把小车当柴火烧了,这样的交通工具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讽刺,应该化为灰烬。安生坐在轮椅上编筐,柳青说,安生,你的手是双好手,别埋没了,搭个棚子开间诊所吧!
安生精通中药,识百糙,辨千花。马回回摘下面具问安生,我这脸能治不。安生吼了声我日,过了一会说,有两种药能让你的脸好看些,一种是白蛇衔过的三叶糙,另一种是麋鹿叼过的七色花。马回回叹口气,我还是把这面罩戴上吧!安生在各地收集了很多单方,柳絮能治脚气,葛根加黄芩能治头痛,加葡萄藤能止咳化痰。1998年,安生整理出版《民间单方汇编》,当年洪水暴发,瘟疫流行,其中记载的被灾区人民广泛采用。其组成成分有:丹参,香附,雄黄,甘糙,陈皮,赤小豆。
安生会刮痧,用一枚清朝的字钱就刮好了我爹的腰痛,所刮穴位是:阿是穴,悬曲至腰俞,腰眼,肾俞,志室,委中。安生最擅长的是针灸。针灸包括针法和灸法。灸法一般采用艾绒。我和叶子常去采摘开黄花的艾糙送给安生,安生便给我们两颗宝塔糖。有一回,一个便密的泥瓦匠被抬到了安生的诊所,泥瓦匠捂着鼓胀的肚子直叫唤,脸已经憋的发紫。安生净手洗面,针涌泉,灸大肠俞,上巨虚,用燃着的空心艾炷迅速点在列缺穴,只听啪的一声,安生说好了,一会儿,泥瓦匠的肚子咕噜一响,放了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