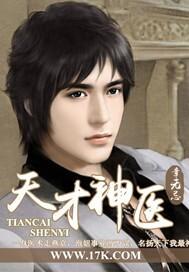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迷谍香精油白天可以涂脸吗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虞从舟心下怅然,世道维艰,究竟几时得安。
“钱币拿着吧,我不会叫人来抓你。”他又把钱币塞回她手里。
“不要,不要,”她仍不敢收。推托间,她的手掠过他的手指,她忽然微微蹙眉,细细摸起他修长的手指,揉搓他每一关指节。虞从舟正好生不解,却听她说,
“大人可是这四五年来,桃花运途始终不畅,虽有美人在侧,却可惜美人冷若冰霜,情心难测?”
“你……”
“大人的桃花结结得太紧了,必有桃花劫。”算命少女抿着嘴,一板一眼地说。
虞从舟心头一凉,本欲求佳言,却得了劫批,难道他和江妍,终是不能两两情深?
樊大头越听越烦,几步枪过,拨开小令箭的手嚷道,“胡说八道!俺们虞爷的俊帅、天下无双,多少女人痴心醉倒!他桃花运不畅?!那你这土豆样儿,肯定只能便秘了!”
算卦小瞎撇了撇嘴,慢吞吞说,
“这乱世之中,英雄难登顶、俊颜难得心,又有何出奇?”
樊大头最不爱听文绉绉,一把扯下她蒙住两眼的黑布带,喊道,“死瞎子,看不见俺们爷的俊颜,算你走运,不然帅呆你!”
无物遮挡,虞从舟见她双眼上皆有难看的疤痕,原来她失明并非疾症,而是受过伤害虞从舟见此情形心生歉意。
算卦小瞎只是憨憨一笑,一边蹲在地上摸索遮眼带,一边说,“这位大哥想来不幸已久,常见俊颜,日渐呆蠢。”
樊大头直想揍他,虞从舟挥袖制止,沉沉说,“樊大头,休要无礼!”
他拾起那条遮眼带,递还给小令箭。只是脑海中挥不去她方才说的桃花劫,轻叹一声,转身零落一副孤单背影,对众门客说了句,“走罢。”
小令箭听他语气悲凉,心中暗笑。一转念,又一本正经说,“大人莫要悲伤,你桃花结虽紧,但近来你骨骼之中金气横溢,正好金克木,如今桃花结尽已散去,今日便是那起承转折之时。从今而后,定是红鸾高照,鸳鸟双飞。今生情浓,来生不换。”
虞从舟闻言全身暖了个遍,回头定定看着她眼上黑布,忽然好似纯呆症附身,半天才吐出一句,“你怎不早说……”
他脸上止不住笑意,只得用拳背抵上下唇,不叫路人看见。眼角眉梢的欢愉之意却肆意漫扬。他再不搭话,从怀中摸出一只鎏金小玉兽放在算命小摊上,转身上马,向一士安欢踏而去
……
众人走远,小令箭席地而坐喝了口水。小盾牌爱不释手地摸着那鎏金小玉兽,心想、主人不是说那虞从舟心思百转、最难摸透,怎么今日如此好骗…不觉咕哝了一句,
“此人…好像甚呆!”
小令箭呵呵地笑,小盾牌又说,“不然,怎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小盾牌噘了噘嘴,“我哪里像是个哑巴!”
小令箭笑得更欢实了,“所以说,陷到情字里去的人都呆蠢。没听人说么,‘爱能叫懦夫变勇敢,能把呆子变聪明&039;。”
小盾牌哼了一声,“他哪里变聪明了?!”
“大概他原本太聪明,掉到情涡儿里反而就呆傻了。”小令箭摇头晃脑地笑,摸过小盾牌手里那只鎏金小玉兽,轻轻咬了口它的小脑袋,润润凉凉的,果然是好玉。
“快换衣裳罢,”小令箭收了算命摊,对小盾牌说,“接下去要做的事儿还多着呢!
……
马儿跑得太快,虞从舟到得一士安的时候,连戏牌子都还没挂起。他寻了正中一席坐了下来,要了壶茶,茶到了又不敢喝,怕待会儿关键时刻打个水嗝,或憋个三急,总不雅观。
一士安是邯郸城中最大最热闹的酒楼,雕梁画壁,红墙墨瓦,高高挑挑共有三层,每层还分东西两阙。东阙是酒场子,时而会请南乐舞班舞几出助助酒兴。西阙是赌场子,六博斗鸡样样俱全,外围还有一圈包间专供豪注之人。
又过了一、两炷香,正等的百无聊赖、唇干火旺,忽听西阙赌场子里有人哈哈大笑道,
“早就说我今日行东风运吧,你们偏不信!”
这个声音好生熟悉,半柔不娇,装沉愈清,虞从舟俊眸扫去,珠帘之后那个清瘦人影、倚在赌案边,面容竟似是方才那街角算命的男装少女,但现下根本没再蒙什么黑色遮眼布,眼眶眼皮儿上更没有什么狰狞疤痕,反而一双小媚眼眨得晶亮。
虞从舟惊诧地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方才街上明明一副可怜却不求怜的倔强小样儿,一幻化、怎生就变得淘气加点妖气的得意百八万儿?
他愣愣出神,还没想起来眨眼,又见旁边个子高些的那人兴奋地上蹿下跳,把赢来的钱币呼啦啦都收进小袋中,分明就是刚才卖艺的哑巴小鬼,现下居然亮着嗓子冲对家直喊,“买定离手,您别往回拿呀!”
瞎子成了眼尖的,哑巴是个嗓门大的……虞从舟郁恼地眯着两眼,本以为自己朝堂上阅人无数,不料今日竟这般轻易地着了这两只小鬼的道儿。
他一排手指“嗒达打大”地在酒案上敲着轮回,盯着那二人心中好气好笑。此刻她们俩依旧男子装束,不过衣着光鲜,全不是之前的粗布旧衣,虽不似富家子弟,但也绝不是贫寒人家。
扮过瞎子那个,额上围了一道翠绿色的锦带抹额,细带正中嵌着一枚白色小玉,淡玉翠锦勾勾勒勒,倒显得她好生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