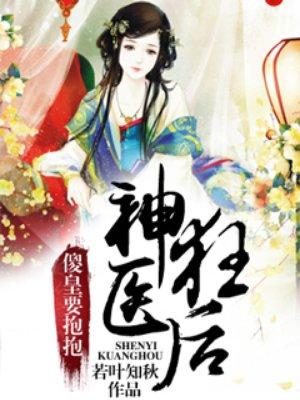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吾妻真乃神人也 宣蓝田 > 35 第35章(第2页)
35 第35章(第2页)
虞锦浅浅白她一眼,也不反驳。
这回她没像往常一样果断拿主意,指腹磨蹭着算珠,慢腾腾地拨|弄了半天。
她没做过粮食生意,京城粮食什么价倒还听过几耳朵,陈塘的粮价却不清楚。可粮食本就是薄利多销的买卖,开个铺子卖腊八粥食材,点子讨了个巧,却也只能比别的小贩贵个几文,不然客人宁愿绕远路去买。
这么想着,虞锦便开口:“这点子倒是不错,真要做起来却没你们想得那么美。”
“啊?”几人都是一惊。
“时下百姓一般喝的都是小米粥,腊八粥里边的花生大豆什么的,都比谷子要贵,不过是腊八这几天图个新鲜,过了这半月就没什么人喝了。而今天已经是初四了,就算你们明儿去村里进粮,后天就把店开起来,生意也红火不了几天,腊八粥撑死了喝到腊月十五,过了这些天,生意就要走下坡路了,兴许连本钱都赚不回来。”
兰鸢刚才还喜上眉梢的,这会儿兜头淋了一盆凉水,苦了脸。
冯三恪和另两个少年也有些丧气了。
虞锦却笑道:“像这样的叫时俏货,一时走得俏,比如冬天的炭炉,夏天的蒲扇,都是这个理,过了旺季就难卖了。做薄利买卖,谁家的价都差不多,比的是新意。怎样留住客,怎样招揽回头客,甚至叫回头客帮你宣传,一传十十传百,这才是能耐。”
四人都垂头丧气的,没人仔细听她讲道理了。虞锦也不讨嫌,话锋一转:“倒也不是不行。”
“先说这腊八粥,好些人家手笨,熬腊八粥就把食材全倒锅里随便熬熬。你们呢,不要卖散称的粮食,你们将各种食材配起来,包好,一包是一锅的量,小米多少、红枣多少都配好,一份一份得卖,这样就能卖得贵一些。要是有心,还可以再备上一张单子,上头写明白锅里该先放什么,熬多久再放什么,如此不愁回头客。”
“这是其一。”
“其二,过了腊八就是年,大过年的,哪怕再穷的人家都不会吝啬,正是做生意的大好时候。那你们说说,过年什么东西是必须买的?”
弥高抢了嘴:“新衣新鞋帽子!”
“春联、福字。”谨言道。
“鸡鸭鱼肉。”这是贪嘴的兰鸢说的。
虞锦挨个白了一眼:“都是不食人间疾苦的败家子。”
她说这话时谁也没看,只盯着冯三恪的眼睛,“掌柜的仔细听,他们仨不知道陈塘什么情形,你该是清楚的。”
冯三恪懂了她的意思,以前他娘和嫂嫂都在,家里琐事不需他操心。可到底是穷苦出身,耳濡目染的,比弥高几个要清楚多了。
“乡户人家,一件衣裳穿三五年,过年买新衣的少;春联福字也少有掏钱买的,找村里会写字的童生老爷帮着写一副,送两颗菜也就是了;鸡鸭鱼肉,这也是有钱人家吃的,穷人家只在年夜吃一顿肉饺子,能省一点算一点。”
虞锦接了句:“县城里比乡下要好一些,可这几样生意都是你们做不来的。”
她一扬下巴,示意冯三恪继续往下说。
冯三恪难得与她心有灵犀,一时竟笑了出来:“唯独一样东西,过年谁家都不会省。”
兰鸢急了:“是什么你快说呀!”
冯三恪没看她,仍望着坐在椅上的虞锦,四目相对,他心口扑腾得飞快,脱口而出:“是零嘴。各种味道的花生瓜子,八仙果、蜜饯、灶糖、番薯干、麻花、狗牙儿、鱼条……每家都会备上三五样零嘴,拿来哄自家孩子,客人来了摆出来也好看。”
“就是这个!”虞锦笑了。
见其他仨孩子还愣愣怔怔,她拿算盘挨个敲了一下,恨铁不成钢:“店是死的,人是活的,那么大个店只卖点零碎你们亏不亏,要做就做大的!”
“时下小贩都在路边支摊儿,卖烤红薯的摊儿上不卖炒瓜子,糖炒栗子店里头没有麻花,卖冰糖葫芦的不卖糖人……咱们那么大一个店,就把这些零嘴全凑一块,弄个大杂烩出来,兴许会有意外之喜。还不止是腊八,接下来的二十三祭灶,除夕、过年,一直到正月十五,家家走亲访友的,零嘴是离不了的。”
谨言愣愣道:“可我们不会做呀。”
“府里厨娘会做好几样,你们跟着学来,会做的就自己做了拿去卖;府里头不会做的,就把街边卖这些零嘴的小贩全请到咱们店里去当师傅,每天做了多少给他们按份算钱,再每人加一份工钱,谁不乐意?不比外边支个摊儿吹风好?”
谨言舌头都捋不直了:“那、那得来多少客人啊,咱能忙过来么?人挤人的,出了乱子怎么办……”
屋里诸人都啐他笨。
“别人都怕没客人上门,偏你怕人多!府里这么些人都能去搭把手,有护卫有零工,还不够用?”
虞锦伸手一指冯三恪:“再说,那不还有掌柜的压阵呢嘛。”
明晃晃的烛火把整间屋子照得亮堂堂的,冯三恪愣愣看着被围在中间的那人,一时失了神。
这一瞬间,他心中踌躇满志,怀揣着巨大的欢欣,以及生平头回被人委以重任的惶然无措。
仿佛站在狭缝之前,有幸窥得商道一角。
听了她的话,冯三恪却摇头说不是。他抿了抿唇,似乎有些难堪,半天憋出一句:“有钱,便不受欺负。”
这是冯三恪最近这半月才生出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