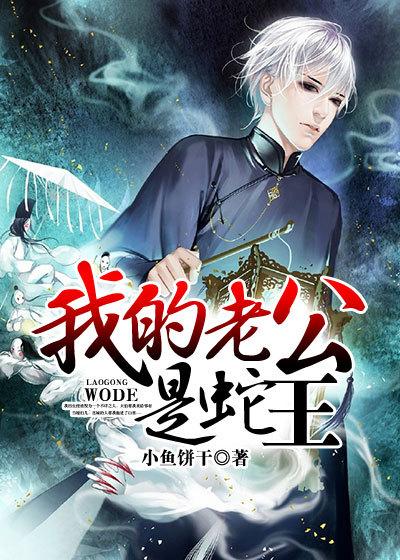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晏殊最有名十首词 > 33 第三十三章 轨迹(第2页)
33 第三十三章 轨迹(第2页)
他竟在琢磨,卫晏应当是恨他入骨的吧?
还没等他确定答案,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流失。
答案其实是肯定的,卫晏自然是恨他入骨的。
但谁也不知道。
卫晏阖上眼睛的那一瞬,脑中曾忆起过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在边塞恣意纵马,在高山之上杯酒言欢,在飞流之间挥剑疾舞的快意年华。
他们曾经是朋友。
至少曾经是。
因为下一瞬,衡澜宗数百人惨死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都知卫晏向来淡漠寡言,可却从来没有人知这并非他的本意。
他也曾年少恣意,也曾快马江湖,也曾骄傲如火。
可偏偏。
满门皆被屠。
满门皆被辱。
清风之剑到头来成了世人嘴里的邪之剑流。
再骄傲的少年郎,再天赋异禀的剑之新星,也难以逃脱复仇的牢笼。
三年有余,他刀尖舔血,无数次倒下,又无数次从血泊爬起来,为的就是清白二字,可灭门之真相始终无法浮出水面。
他痛。什么时候痛?
刀剑穿透他的胸膛时,他没有觉得痛。
世人以言语击刺他时,他没有觉得痛。
可在抬头望见数个寂寥深夜的月时,他觉得痛。
无力。
是深深的无力。
是望不到尽头的无力。
是一点渺茫希望全无的无力。
卫晏从季楚撞上他的剑到他死了都始终缄默不语,他只是如同行尸走肉般抽出自己的剑,盯着剑上的血,再也没了动作。
大仇已然得报,但他的心里却未曾松解过半分。
因为至此,给他短短前二十几载留下浓重色彩的人,都已尽数离去,他又是孤身一人。
沈舒舒的大脑也跟着停滞运作一般,她的心开始微微绞痛。
整个京云峰蓦然安静下来,出奇的,没有人开口说话。
毫无征兆地,卫晏跪地倒下。
“晏晏!”
沈舒舒心尖猛地剧烈一跳,她着急忙慌地向卫晏跑去。
她颤抖着手捧起卫晏的脸,发现他往日红润的唇此时竟变得毫无血色,身上的伤也未曾停止渗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