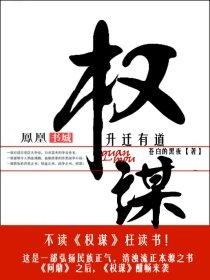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六宫粉黛无颜色前面一句 > 第518章(第1页)
第518章(第1页)
孩子爹这才安静下来,憋着不吭气了。
定柔歪了歪头,就昏睡过去了。
这一觉不过略略阖了阖眼,再醒来竟是翌日下晌了,小摇床里的那位呱呱呱哭不停,奶母抱到隔间去喂奶了,孩子爹还在身畔,穿的仍是昨天那身朱红深衣,两眼乌黑,定柔诧异不已,他不会没上早朝吧?
问了月笙,那厢支支吾吾答:“太医说这一夜最凶险,怕再发了血崩,陛下担忧您的安危,未曾离开一步,让他们传口谕下去,说圣躬不豫,暂罢朝一日,有事拟奏本来看。”
定柔身上恢复了一丝力气,操起一个绣枕迎头扔过去:“你这不是上赶着让人说我是红颜祸水么!你这个误国殃民的昏君!”
皇帝见她有了精神正高兴的厉害,一把接住了枕头,捧在怀里嬉皮笑脸说:“就这么点子力气,有本事你起来拿蛮锤教训我!”
定柔咬了咬牙,还真要撑着坐起来,这一动身上似被无数利爪撕扯着,疼的冒了冷汗,皇帝吓了一跳,慌忙投降:“你别激动,我这就回昌明殿。”
嘱咐了宫人们几句,深深看了孩子娘一眼,这才掀幔而去。
到了外殿活了活动酸乏的手臂,命小柱子:“一会儿贵妃睡了,让何嬷嬷去趟陆府,将实情告知陆绍翌,把慕容府的人也叫上,就说是朕的旨意,闹他们一场,贵妃这委屈不能白受了。”
小柱子“喏”了一声。
皇帝嘴角含着一丝笑,陆绍翌,他再也不是我的威胁。
下了玉阶,忽又想到了什么,回头道:“你亲自去趟骁骑北营,把陆绍翌从前的旧部下召集二三百人来,围了陆府,把内仪门也围了,不许人随意进出,将奴仆们细细盘查一遍,凡日用之物经御医查验,明着就说陆绍翌在敌境蛰伏数载,有通敌之嫌,朕要防备细作串通。”
小柱子继续拱手说喏。
皇帝转而上了肩辇,这当口得防备有人暗算,那小子若遭了毒手,我和定柔之间岂非下了一个死结,这一生背负着愧疚。
何嬷嬷领了口谕不敢耽搁,坐上轿子回慕容家叫了王氏和另外几个妇人,去了陆府,李氏母女见到她们就知来者不善,本要拦着,何嬷嬷直接搬出了圣谕,阻扰者抗旨论处,这下子骇的李氏和陆绍茹不敢说话了。
陆绍翌独自屋子里灌闷酒,打算醉生梦死,被小厮叫到凉亭,何嬷嬷从袖袋里取出休书给他看,抹着泪将当年十一姑娘分娩前后,安西都督府的讣闻送来,姑娘坐着产褥冒雨跑了出去,不慎摔破了头,伤心之下骤然没了母奶,可儿小姐从此断了吃食。狠心的祖父母和姑母、庶出的祖母无一不是心肠恶毒冷酷的,襁褓里的小婴儿整整四天没有吃到一口奶,她们无所不用其极,十一姑娘被带到柴房动了毒刑,指头都快夹断了,全身伤痕累累,还险些被卜姑爷糟蹋了,问问黄天老爷,有这样对待一个月妇的么。后来,几人半夜砸锁逃了出去,十一姑娘只剩了半口气,小婴儿哭声微弱,是皇上及时出现才救了母女俩的性命。
何嬷嬷说到前尘往事几次哽噎不能语,那些历历在目的,无不是血和泪。
“陆公子啊,若不是皇上,你回来看到的是母女俩坟前的黄土,只怕草都一人高了,皇上恩重如山,姑娘便是以身相许也不为过呀。你怨她辜负你,可她对你情至义尽了呀,她从昏迷中醒来得了失魂症,不认人,不会吃喝拉撒,和傻了没区别,她那般要强的心性这是多大的打击啊!可就这样,她病愈之日还要为你殉情,就在悬崖边上,带着可儿小姐,若皇上晚到一步,你今时完好无损回来岂不阴差阳错,你不心疼女人,难道连亲骨肉也枉顾么,是皇上一片痴心打动了姑娘,她到底是一介弱女子啊,陆家休书在前,十一姑娘入宫在后啊”
陆绍翌听得肝心若裂,身躯凛凛地颤,攥着休书,看着上头的一字一句,泪光模糊了视野,转头去看立在一旁,脸色如菜的母亲和长姐,红着眼问:“你们虐待定柔和孩子了?你们”
陆绍茹狡辩:“弟弟,你信她们胡编乱造!你信外人不信至亲么,分明是那姓慕容的小妖精有了二心,抛家而出,还陷害我谋财害命,让我住了一年多的大狱,不信你问娘。”说着扯了李氏一下。
李氏心中发虚,硬着头皮附和。
王氏和其他夫人争辩起来:“我们作证!我妹妹若不是在你家九死一生,怎会闹到大理寺公堂,她的嫁妆被哪个黑心肝的吞了,到是说说啊。”
陆绍茹掐腰喷着口水对骂:“哪个才是黑心肝的,不就因为慕容茜那小贱人能给你们挣来荣华富贵,让你们穿上诰命夫人的皮,一起来栽赃我家!她的嫁妆谁见了,去搜啊。”
一时间口沸目赤,各不相让。
陆绍翌想起枕边人的品格,她绝不是三心两意、朝秦暮楚的女子,若当初爱慕荣华,怎会选择一个无权无势的陆绍翌,昨日昨日
何嬷嬷抹了一把泪说:“陆公子,做人不能失了良心,这些年皇上待可儿小姐视若己出,便是铁铸的心也该化了,你想想,若陆老爷和太太怜惜孙女,孩儿怎会无人收留,入了皇家的宗牒,太太当年说,一个丫头片子还不如没有,老婆子对着黄天焦日起誓,若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
陆绍翌呆呆望着休书上的几个红手印,喉中格格地响,五脏六腑如被千矢万镞攒绞,那两个响亮的巴掌打在她身上,一定痛极了将她的心打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