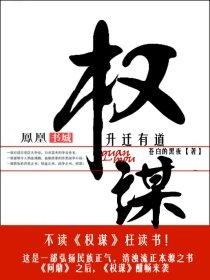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灵道师 > 第二章 人前受辱(第2页)
第二章 人前受辱(第2页)
今天你敢往我裤裆里抹粑粑,明天我就敢你给我舔皮燕子。
我陈侃说到做到。
苍蝇围在我的头顶上嘤嘤嘤嘤的乱飞。
我一头扎在水缸里,仇恨莫名的升起。
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受辱,也是唯一一次。
我把身子涮了个干净。
正要起身。
一个纤瘦的身影向我款款走来。
我也顾不上臭了。
一头又扎到水缸里。
“侃爷,你快钻出来吧!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身子!”这声音我熟,我露出头来。
不白姐?
我带着这个问号赤条条地钻出这臭臭的水缸。
我有千言万语都来不及问她。
不白姐把一身崭新的衣服递给我。
“快换上吧!”不白姐的双颊透着红润,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我想过了,我不该走,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今后,我们得对彼此负责。”不白姐脸上的红晕越说越多。
她没有说这半年来她都去哪儿了。
我换好衣服后回头搬起一块石头就把大缸砸了个粉碎。
粪水淌了一地。
“想明白没?日子还得过,这顿打可不是白挨的!”不白姐拾起筐来。
我俩一前一后出了门。
我那一肚子的问号不知为什么全都烟消云散了。
我乖乖地跟在不白姐身后,就像她亲弟弟一样,一步也不舍得离开。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她不白姐究竟是不是天上派来保护我的,反正就是从那时候起,吴老二那一伙子人就没敢再去过我家。
就连在路上碰到我们,他都故意绕着走。
就这样不管晴天还是下雨,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冷酷无情的寒冬。
我们一天都没有耽误过。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蒙住我的眼睛,突然问道:“猜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我想都没想就说出了她手中拿的是什么药,还把这种药的主要性能和重量全都说了出来。
可是不白姐还是不敢相信,又接二连三的拿出很多草药来让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