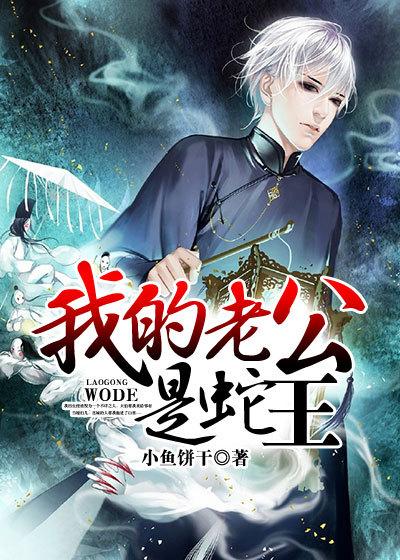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盲狙cs > 第99章(第2页)
第99章(第2页)
“你就是你,与任何人无关。”
“想走可以,别走太远。”
“苏婥,我从没收回过给你的底气。”
“苏婥,你当我什么?”
“你还想要什么身份?当年你怎么说的?”
“是你说想跟我。”
……
太多的话,像是一瞬之间开了闸,汹涌吞泄似的外溢而出,砸在滚滚鸣雷下,重戾刺激着现在这个麻木不堪的苏婥。
翻来覆去地,苏婥最终没能承受住心理的压迫,眼泪肆意淌下,温热滑过耳骨,堪堪坠落在绵白枕边。
周围的空气像是越来越稀薄,压制着她的呼吸,她眉心紧皱,哭不出声,可又哭得这么难受痛苦。
梦魇太煎熬了,她亲眼旁观灯塔的爆炸,旁观男人离她越来越远地摔落深海,溺入冰冷寒水。
像是冰锥霎时刺进脊骨,她却根本就无能为力。
伴随着外边再度炸裂的窒息感,苏婥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
最后那下引起整栋郊区别墅都震颤的爆炸,轰的一声,苏婥猛然间梦惊睁眼,胸口上下强烈起伏着,视线涣散,半天都聚焦不到天花板的任何一处。
她抓着床单的手劲不减反增,连指尖剐蹭疼了都感知不到。
唯独有的,是满心的惶然和难言的失落。
那个男人是谁?
她为什么会失落?
无论苏婥怎么费劲心思,都在记忆中找寻不到答案。她知道可能是最近生意链在加急,自己太过敏感,便没多想。
可梦的开始,就代表着后来的接续不断。
像是心里住了个人,不放弃地紧紧攥住她漠然的心脏,每一下跳动都受限,非要逼出她的疼痛。
终于,苏婥受不了了,服软了。
她开始尝试妥协,开始试着去找寻这段荒谬记忆的初端。
直到那次无意路过厨房,苏婥撞见佣人专门在给她那份西餐外加着不知名的白色粉末,苏婥才后知后觉问题所在。
她刻意留了部分去私下做检查,才知道这是阿立哌唑和奥氮平,抗精神病药,是程控怕她好转变回从前的手段。
苏婥想起祁砚的过程太过艰难了。
她一次次地暗地挣扎,一次次地怀疑自我,唯独没把对程控的恨意表露在外。
除了接二连三的梦境,苏婥还在私下找各种能帮助恢复记忆的办法,尝尽苦头,都下了狠心要把祁砚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