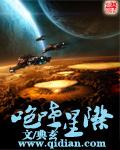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九尾怪猫阿基多 > 第86章(第2页)
第86章(第2页)
这件事得在家里做才行……我得有个可以坐下来而且觉得安全的地方。
当斧头落下来的时候。
行刑台送上门来。
不须额外付费。
他在一个橱窗前停下来,里面有个没有脸的天使,手上拿了一根像针那么细的火炬,想要振翅高飞。他看看表。
维也纳这时正好是子夜。
那么我还不能回去。
还没到时候。
时间到了再说。
想到要面对他的父亲,他就像乌龟被踩了鼻子似的,不敢再想下去。
埃勒里一直拖到清晨4点差1刻才回到家。
而且还踮着脚尖。
除了客厅茶几上的意大利陶瓷灯亮着之外,屋子里一片漆黑。
他觉得全身都冻僵了。街上的气温已经降到华氏5度,屋子里面也只不过比外面好一点点。
他的父亲鼾声大作。埃勒里鬼鬼祟祟地朝房间走去,关上房门。
然后,他偷偷地溜进他的书房,锁上房门。他连外套都没脱。他打开桌灯,坐下来,把电话拉向他。
他让接线员接国际电话。
线路有点儿问题。
已经快6点了。暖气管里的水蒸汽开始琳唯作响,他的眼睛始终警醒地盯着门。
警官通常准时6点起床。
埃勒里一边等候维也纳接线员帮他接通电话,一边祈祷他父亲睡过头。
「你可以讲话了,先生。」
「赛利曼教授?」
「是!」那是一个非常年迈的声音,声音低哑,语气略带焦躁。
「我是埃勒里&iddot;奎因,」埃勒里用德文说,「您不认识我,教授……」
「那倒不见得,」那年迈的声音用英文说,带着维也纳口音的牛津式英文,「你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由于在纸上犯下太多罪行,你的负罪感使你在真实生活中也以追缉不法为职业。你可以说英文,奎因先生,你有什么指教?」
「我希望没有在不恰当的时间打扰您‐‐」
「在我这个年纪,奎因先生,除了思考神的本质时所奉献的时间外,任何时间都是不恰当的。请接着说。」
「赛利曼教授,我相信你认识一位名叫艾德华&iddot;卡扎利斯的美国精神医生。」
「卡扎利斯?他是我的学生。怎么样呢?」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不寻常,一点儿也没有。
‐‐有可能是他不知道吗?
「您最近几年有没有跟卡扎利斯医生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