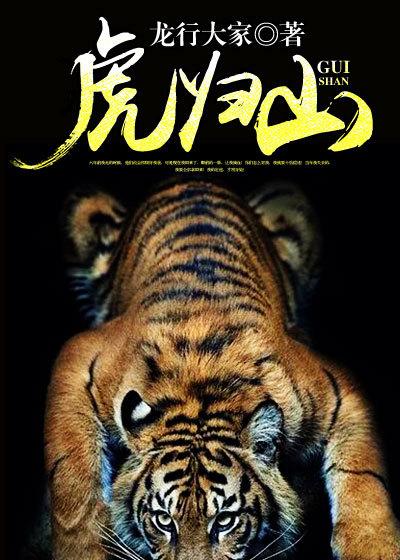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妖僧的枕边人 嫦娥结局 > 25 25魔音(第2页)
25 25魔音(第2页)
她朝应无相窥去,只见他一派闲适,犹如置身事外、百般无辜一般,眉目更是松展安然。
何吕氏说到兴起,不时漏出几声笑来:“这事儿我和村口的几位婶子也说过,她们都说我办事儿麻利,是许多小娘子及不上的,李薛娘子你说是不是?”
薛泫盈一顿,刚要开口答是,只察觉那掌心猛然侵袭向上,竟探入她衣袖,握住了她一截细白的小臂。
一个“是”字,刚转到口中,便被应无相击得粉碎。
何吕氏见她支支吾吾,两耳通红,只当她是腰疼难忍,不愿自讨没趣,遂又含情带怯地朝着应无相望去:“这些话,我说了倒像自夸似的,应二郎听得可烦了没有?”
她问罢,应无相便将目光一转,不咸不淡地落到何吕氏面上,吐句清晰:“何吕娘子,你方才说什么?”
何吕氏面色一僵,半晌愣着,强笑道:“并没什么……我险些忘了,应二郎日日劳累,想来最是想要静心养性的。”
说罢,她颇觉处境尴尬,便挑帘朝外一望:“河州村已是到了,便不劳车夫送进去,我便在这处同二郎、娘子告辞了。”
何吕氏下了马车,还不忘朝车内薛泫盈道:“李薛娘子今日莫觉着孤身一人,明儿我便寻时候,同蓉儿一道搬过来,同娘子做个伴儿。”
说罢,方才施施然去了。
这厢何吕氏刚去,马蹄急起,将轿厢猛然一晃。
薛泫盈恍然抬脸,只见应无相同她不过咫尺距离,两人呼吸相缠,灼热互撒。
她心中难以遏制地传出巨响。
应无相将掌心自她袖中抽回,指腹同她颈下的一缕青丝相勾,卷起又散,任一抹乌黑漫入她颈下胸前。
他的右臂将薛泫盈圈揽其中,低声相贴:“好盈娘,莫不是觉得,某对那何吕氏真有非分之想?”
这句话传入薛泫盈耳中,却并不动听。
她唇角一扯,难得地露出几分讥色来,十分生动:“应二郎。”
唤过他这一声,薛泫盈便撑起身,颇坚决地同他撤出些许距离。
“如若二郎知晓同何吕氏并无结果,不若早早表态,同何吕氏做个了断,也好让何吕娘子不付真心、及时脱身。”她说得极缓,“二郎在我这儿同何吕氏有所区分,在何吕娘子那儿却又不乏关怀挂念,谁又摸得清二郎心中所想?”
应无相定定地凝着她,刚要开口,又被薛泫盈出声拦下。
“莫说我与应二郎,应二郎与我皆是孤家寡人,便是受些暗伤、吃些哑亏,也使得用一句‘吃亏是福’来自我宽慰。可何吕娘子尚且带着一位身娇体弱的女儿,她若受罪,难免牵连孩子。”
她说罢,方才对望回去:“应二郎,你既有入佛拜教之心,合该存有慈悲悯意,不该如此将真心戏弄,折损福报。”
这些话听来是难得的硬气。
待自己说罢,薛泫盈心中颇为松快。
她朝应无相觑去,只见应无相笑色寡淡,两目深幽:“什么真心?李薛娘子是说那贪慕钱财、求一寄身之所的真心吗?”
此话落定,薛泫盈一怔。
“何家郎为何吕娘子母女二人入狱,将受断头之罪。未死之际,何吕娘子便盘算他家,求的并非真心,而是家中田亩几何、积财几许,后有蓉姐儿跟着,前有杀人掠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