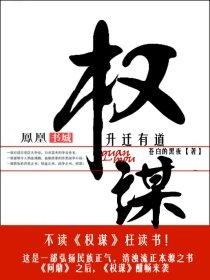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妖僧的枕边人免费阅读 > 5 5小鱼干(第2页)
5 5小鱼干(第2页)
应无相便无端想起了昨夜薛泫盈托递碗盏的手。
他喝了那碗酒后,情动难以自抑,泼洗了四通冰冷的井水才堪算消停。可妇人的一颦一笑、一行一止,却犹同烙在了他眼前般挥散不去。
尤其令应无相惊疑的是,那一晚并无梦魇惊扰。
应无相是永安巷中勾栏瓦舍的风尘女所生,这是孟西村里头各个儿都心知肚明的事实。
在他诞世以前,他的生母荔娘是个样貌艳丽、性情如水般的女子,虽被卖为娼妓,却仍钟爱抚琴奏乐,颇有雅兴。因此,荔娘接待着众多文人墨客,奉几盅酒、唱数支曲儿。
亦与楼中女子一样,荔娘日日饮着避子汤,以恐断送了风月场的生意。
可即便如此,荔娘仍是怀上了他。
应无相不知其中真假,只知晓街巷百姓们口中津津乐道的版本是,荔娘腹中揣了野种后日日忧心,想来不日事发后必然被楼中妈妈逐出去。
是夜,荔娘饮下一盏红花,势要除去腹中未成形的胎。
惊奇的是,即便是一盏红花,也没能夺走腹中孩儿的命,却夺走了荔娘的半条命。荔娘翌日竟疯魔起来,口中痴痴念着疯话,道是孩儿夜间托梦与她,诞世便要夺她性命!
那一夜过后,荔娘便成了街上日夜游荡、痴傻成性的疯妇。而应无相还未出世,便被冠上了“妖胎”的名号。
那年冬日飞雪,荔娘于雪夜当街难产,无人问津。诞下应无相后,果真被他夺去了性命,应了那夜的托梦所告。
孟西村中好心的村医将荔娘安葬,又将应无相拾走,令他过了几年温饱日子。不料好景不长,仅仅六年过去,村医便在梦中暴毙身亡。
此后,应无相便彻底成了街头巷尾口中的“不吉之兆”。
他已记不得,自己是如何与刽子手这三个字牵扯起来的了。
只记得村医死后,他终日以拾荒为生,同野狗嘴里抢吃食;日子若再难过些,过路醉了酒的男人、不如意的女人、成群结队的孩童,抬脚便能任意欺辱于他。
那日应无相活剥了一只野狗,开膛破肚、尸首分离。
原本上赶着来欺辱他的孩子们,惊恐尖声着四散开来,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他望着手中热乎乎的血,却在冬日感到久违的温暖与安适。
壮硕的男子走到他身后,望着应无相手中的尖刀,沉声问:“你缘何要杀它?”
应无相缓缓摇头,指着野狗泛黑的胃,漠然:“我未曾想过杀它,是它中毒垂死。我只是想瞧瞧它吃了什么,好让我往后避开。”
男子一愣,继而低声笑了起来。
应无相回过脸,对上一张满是刀疤的长面——那便是将他引上刽子手之路的的养父应缙,亦赐他“无相”二字为名,好让他也能够有名有姓地活下去。